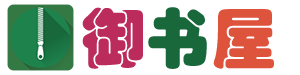今日出门,用了三辆牛车,四队护卫。零零总总统共三四十来人,最近世道不太好,随行的护卫穿了软甲带了兵器。走在车边发出“嚓嚓”的摩擦声,挑帘望去,只能看到一个个面无表情的侍从。这条街好似为她而清场。
车架刚进入张家门前的道也已清场,仆妇丫鬟们都在门口立身恭候,砚心递了帖子去,上次来迎张娘子的婆子一边春风满面地接过来,一边恭维寒暄。
“谢七娘子可有劳累?”
“我们府里恭候多时。”
“……”一句接一句,谢溶只能回复“我亦然”,“也不曾”等。只觉得自己像一只牵了线的木偶,同她说话她便回答,脚步也不能停,亦步亦趋地跟着引路的使女。
穿过游廊,走进到一处院落,一路草木催发,早莺鸣啼。只是她现在人言鸟语已经分不清了。众仆把她们引到一处香榭,便守在了门口,早有人进去通传了,还有搬着花盆,捧着香案,点心的侍女三三两两。
刘媪看见张二女郎还在歪歪地躺坐在榻上,不起身迎客,有些急躁了“女郎,哎呀女郎~”不过张若心依旧一副淡淡的神情倚在一边看书,全然无起身意思。
张若心见刘媪脸色焦急,又不好在外人面前说教的样子觉得有趣极了,才放下书,展颜道:“我知道了。”起身给谢溶拜了个礼:“谢娘子安。”然后嘱咐刘媪:“将陆先生请来。”
“这,这,都是女郎在,请他做甚?”刘媪大惊失色:“使不得,这陆先生是…虽然…但…但是…”
“刘媪放心谢家娘子不是别人,陆真人可与谢娘子兄长关系匪浅呢。”张若心遣散了屋内的丫鬟仆妇,招呼谢溶坐下,诚心一拜: “上次应该多谢娘子的,只是我那时心不在焉的没了礼数…”
“不,不…没事的。”谢溶第一次和同龄贵女接触,谨记着昨日顾夫人的嘱咐,说话也颇多顾虑,一时间不知如何接话。张娘子似乎看出了她的窘迫,说道:“我伯父阿叔们都是武将,自小在他们身边长大,我是野惯了的,听说谢娘子也是从小在外面长大的,与我不必拘束呢。”说罢递给她一盏茶:“你既是谢思行的妹妹,我比你也略大一些,你也是我妹妹了。叫我张姊姊就好。”
水榭点了暖香,谢溶鼻尖冒了一点点汗,听她念着谢令殊的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谢令殊情愿拉自己下水也要救她出来,想必张娘子对他真的很重要。可之前并不是自己去招惹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后来却为何一直对自己冷眼相待。
张若心看谢溶不说话了,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只是等下有事央她帮忙,还是要先套一下近乎的。
两人刚喝了一盏茶,有叩门声传来。
“哼~”只听张若心冷哼一声,声音又恢复冷冰冰的样子说道:“这地方未必有门关着?”全然不似在谢溶面前的和蔼可爱。
“咳咳~咳~“听到这阴阳怪气的话,心里一惊。想着这女郎变脸的技艺真是惊世骇俗,到底谁惹了她?
“女公子万福慈悲。”门口出现陆真人的身影,他体量清高,蓝衣素带。在门口时候挡了一部分日光,走近一看,那白面竟蓄起了须。只是眉目依然清冽如霜。
谢溶一想便明白了,自己回去不过几日就收到了帖子。想必是那天陆仙长同他们一起回城竟不是回的谢家,而是住在张家。可是他找自己有什么事呢?
比起谢溶的好奇,张若心只觉得内心烦躁,看着陆宾然的面庞气不打一出来。要不是有谢溶在场,她怕是要去揪掉他的胡子。
陆宾然却仿若未觉,自顾自地坐在离她们远一些的椅子上。眼睛瞧着张若心放在一边的书,哦,《南华经》。也真是难为她看这些书了。
然后不动声色地移过目光,看向谢溶,笑到:“谢善主贵体可有好些?”
谢溶知道自己的药是他配的,也不讳疾忌医。答道:“视物并无大事,只是久了眼干。”看陆道人还在看着自己,想了一下,又继续道:“身上到了半夜还是有点痒…”
此痒非彼痒,就算是面对医者,让她说出来也怪难为情。眼下还有张娘子在,陆宾然眼看着她,似乎等她再说下去。
看出来了谢溶的些许窘迫,张二娘子适时开口了:“你一定要大家都尴尬么?”
本应该感激她出面维护,但是这话说的倒是尖锐得让人更尴尬了,谢溶立马摆手:“没有,不是…我~~~”
饶是谢溶再傻也能瞧出这张娘子是循着一个契机便要为难陆宾然的,不知道他们两人到底有何过节,自己还是闭嘴免受波及吧。
不过这陆宾然听她这话也还是镇定自如,被下了脸来也不生气。从袖笼里拿了一个瓶子,“这个是贫道新炼制的药丸,用法与之前一样,敷眼洗眼的药物,已让人拿给谢善主的家里人了。”
然后他看了一眼张若心,又笑着对谢溶道:“我不打扰二位女公子,便长话短说。”
看他还有话说,谢溶好奇,难道是他让张娘子请自己来的?
“是我拜托张善主请您来的,令兄的身体并不大好,我也为他带了药。只是我们偶生龃龉,他对我颇有微词…”话里虽然表示二人似有矛盾,脸上却一派正义平和,说的好像只是幼童拌嘴一般。
这更让谢溶好奇了,难道是要让自己做个和事佬?
“这,需要我做些什么吗?”谢溶摸不准他的目的,也不想去猜,当然她更不想探究他们之间的事情,太复杂了,也不是她有能力涉足的。更何况,她也已不知道用何种面貌再去见谢三郎。
看出她的为难,陆真人倒也爽快,又掏出一个白青瓷瓶说道:“令兄仍在气头上,不愿意见我,可我却是一颗医者心…他素有头疼的毛病,请您把这个带给他,以表贫道的歉意。”
谢溶越听越迷糊,但总算是弄清楚了,原来是这陆真人和谢令殊两人意见不一,生了嫌隙,谢三郎疏远于他,他便想让她把药送给谢令殊,以求修复关系。是这样吗?
陆仙长看着一派仙风道骨虽是修道,这凡尘之心倒是挺重啊。她悄悄地在心底腹诽。
谢溶虽不是很愿意和他们接触,但自己的用了陆宾然的药确实好了很多,若是拒绝,有点过河拆桥的嫌疑便应了下来:“我试一试吧。”
谢令殊闭门在家已经好几天了,越是临近清明心情越烦躁,尝试过所有能做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失败后,他干脆喝起闷酒来。
上次让谢溶画的画像确实起到了作用,伪装流民的左卫小将们在一个农户家里抓住了逍遥客。绑了回来,倒也配合,不用刑罚便把证词都录好了。
正等着朝会那日与几个良民一起上殿指认。可是陆宾然却突然像发了大疯,非要把他师弟带走,说是私下解决可以,必不能面见天子。二人言语激烈,不欢而散。
梁帝每五日临朝会,他硬是捱了四天到朝会那日把齐彰和后来捉到的道士带上殿来对质,准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哪晓得这妖道竟被陆宾然偷走了。
朱益自然是作大惊失色状,虽然并未否认齐彰与自己的关系,却矢口否认自己让他们炼药之事,强抢民女更是自作主张。两人一追一躲从上午辩到了午后。几个道士未曾接触过药物,自然也没有证据。两人分庭抗礼,势均力敌。这时候…
“官家明鉴,谁人不知道谢郎君家里与太上道君关系匪浅,他自有道观捐建,请几个道士来演戏也不是没可能。”说话的是朱党的一位孙姓议曹从事,是朱益的心腹谋议。当日接引侯靖,把谢溶拎出来联姻的主意都有他一份。
“道士是假的,受害人莫非也是假的?孙大人恐怕是自己经常演戏,才以己度人吧。”王谢两家是百年之好,先祖也一同南渡,子孙同朝为官,大多在同一阵营。这次开口的是郎中令王赟的一位从弟,叫做王犀廷尉监。
这两人开起了头,一边新党朱益周期等人的亲信便三三两两地拜了下来,说朱将军乃是佛子转世,布施纳捐,菩萨心肠。不想有恶贼竟借此干尽坏事。
另一边世家集团王谢郑袁等人也开始反击,直指朱党假借无遮法会名头大肆敛财,极尽奢靡。
“坏的是不知好歹的恶僧,何人犯法便处决何人,竟把火引到朱将军头上,谁人不知尔等常与将军作对,简直以公报私!”
“小贼一个杀了便杀了,若是他没有后盾,怎可以在玢阳公主的食邑掳掠迫杀良民?”
“……!!!”
(神仙打架,齐彰遭殃。)
“……!!!”
日晷的影子又偏斜了许多。两边仍无退意。
“咣~咣~咣~”左右随侍的内监敲起堂上的铜磬。众人这才骂骂咧咧坐回自己的案后。
“近日朱将军为吾殚精竭虑,谢侍中亦是鞠躬尽瘁…”梁帝看谢令殊死咬不放,何况此事又是在先皇后陵处发生,于是口风一转:“子升(朱益字子升)卿并非无过错。”看到帝王脸色不善但言语间也无迁怒之意,朱益也不是个傻的,当即跪下叩首:“臣下御下不严,万死难辞其咎。臣请求官家放臣去钟离郡,臣押解粮草,抚慰戍军,未有诏永不回建康!”言辞激烈,涕泪淋湿了绒席。
听得梁帝称呼有变化,都嘶了一口气。朱益自请下放出都城,谢侍郎却升官做了侍中,众人这便明白了今上又是想来大事化了。于是各家心思不一,却不敢形于色。
“什么?”谢令殊看朱益跪地如此之快,与梁帝二人一唱一和,不禁怀疑两人早就串通好了,一时间气急攻心。“三郎年纪尚轻,为吾拳拳之心让吾感动不已。”梁帝看他一脸不可置信,恐他再追究又要闹得难看,自己这些年多有疏远他几家,却亲近朱益,士家心中肯定颇有怨言的。
但谢令殊想的却是侯靖降梁以来,大军落脚的老巢就在离钟离郡不远的仁州,他的儿子门客全都在那边。朱益自请去那边,岂不是,岂不是…
“官家!不可啊…”谢令殊急忙起身,却不及朱益反应更快,他咽着嗓子道:“侍中且消气,这次事情是子升识人不明,害了无辜。诸恶莫作,在下万死难辞其咎,可眼下我若饮鸩谢罪唯恐陛下无人照料,鄙人愿拿出二十万石钱粮补偿被害者家人,另出五万石绢帛慰劳泯悲寺庄子里的佃户,日日为他们诵经祈福…”
嘶~朝堂之上又是一阵吸气,二十五万石钱粮绢帛啊!一个五品长史年俸米不过一千石。当下朱党诸人皆下跪口呼陛下。
“朱将军日以继夜侍奉菩萨,自然是有疏忽。我等愿与将军一同受罚。”朱党有权位高者开口了。
“谢侍中自是大义凌然,别人都是虚伪小人,那你又为何不供给吃住给那些受害良民?”
“将军慈悲心肠,愿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是恶贼不争气!”
一下朱将军仁心被人蒙骗,一下又抨击谢令殊咬的太狠,斯人已伏法却还如此凶悍追责,为何不自己出钱抚慰受害者。
几位王谢家这边的势力想是见惯了这种场面,看对面如此厚颜无耻,也齐齐跪下,指责对方竟想用银钱买命…
“你做了恶事找人背锅,他做了恶事也找人背锅。改日当街杀人了是不是也说是刀子自己飞上去的?”
“没有后台他何敢欺到玢阳公主的佃户头上!你敢不敢对天发誓?”
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佛口蛇心的畜生!谢令殊银牙咬碎,恨不能当场撕下他的画皮。明明证据都在,为何如此偏颇?为何如此袒护?脑子嗡嗡作响,竟有种眼前发晕的感觉,谢峤看他脸色不对,拉了他的衣袖。
梁帝看两边唾沫横飞,有人拿起笏板就要打人,一时间眼晕,吩咐左右了几句。便趁乱回了后堂,准备从侧门出去。
谢令殊眼疾手快,正准备赶上去拦住梁帝。谁知袍子的边被人勾住,无奈最近殚精竭虑耗费了不少体力,现在拉袍子都有点手脚无力,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梁帝远去。
听着内监传达天听:“今太常卿、武威将军、尚书左丞朱益,兹不辨菽麦,使小人残民以逞,停其职迁钟离。有谢令殊黜邪崇正,谠【党】言直声,升侍中同任廷尉正……”
明明是他家左迁我家升官,这声音在谢令殊听来却无比刺耳,同样的场景,一而再再而三。
那天回去之后就害了风寒,想是前段时间精神紧绷,又被朱益气到。梁帝闻言派人送了不少珍惜药材经卷典籍,使臣前脚刚走,后脚朱益的礼物也一并送到,除去补品药材,还夹着一卷自己手抄的《法句经》。
谢令殊看着他装模作样一把好手,只冷冷道:“你家将军的二十万石钱粮可有拨下?受害之人名录都在我这,便让谢饶跟着你们去发放吧。”
朱益此人的过人之处中,那诗书和字是绝品。时人附庸风雅好书爱画,虽不齿佞臣却实在难舍这游龙惊鸿般的仙品好字。
谢令殊虽厌恶他,但自己亦是名家之子,收到朱益手抄《法句经》难免也要观摩一番。只是刚打开,开头便是:无常品者,寤欲昏乱,荣命难保,惟道是真。
(翻译:帅哥你最近太爱生气了,须知气急攻心,物质荣誉都是镜花水月,只有大道永恒在是真的。)
这一下竟是一口气没提上来,一口血喷在了经卷上面。如此羞辱,不如去死。
又遣了侍从提了几坛子竹叶酒去水榭。
一醉方休罢,最好长醉不醒。他心想。
酒过几巡,醉眼蒙蒙地看月,月亮也笼在一层薄雾中。前段时间和父亲说起佑真,近来匪患越发严重,他想带佑真住回来。家里的照顾或许能让佑真更好一点。但父亲却不让,可是他又凭什么不让呢?母亲故去后他自己又过成了什么样子呢?
又几盏下肚,他恍然听见女子的讲话声。仿佛说的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是小时候母亲带他读诗经细细给他讲过的。“民生多艰,前朝横征暴敛,如今新政,思行日后做官,要体恤民情。”母亲的朱颜依稀在眼前,谆谆教诲也尚在耳畔。
“母亲,我有在努力啊!”他的泪止不住了,流在了碗里。又顺着喉咙流进了肚里。
树叶落下在水面荡开一圈圈涟漪,水中月也变形扭曲,在眼前放大缩小。深色的湖面像一个黑洞要把人吸进去。
不忍月亮堕入深渊,想伸手去抓住…也或许是想和月亮一起堕入黑暗吧。
——————————————————————————————————
闲话:小珍珠助力哥哥打到职场小人,手撕职场绿茶! 下一章妹妹出场!
可见谢爹爹确实混得不好了,要出差,要一直外派,而且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个长史!!!
运筹失算百念消
同类推荐:
【快穿】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爱欲如潮(1v1H)、
她的腰(死对头高h)、
窑子开张了、
明星梦九重、
草莓印、
辣妻束手就擒、
情色人间(脑洞向,粗口肉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