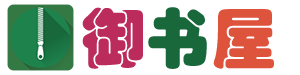长平到咸宁一带东西紧挨着连白山脉同阿勒泰山,只中间一道由北向南的弗尔滕河,一直流进朔州,汇入十方湖。
天寒地冻,定远军正忙着趁夜泼水加固城墙。所幸灏州城连守二十多日终究是守住了,配合定远军在外收回了长平同咸宁两城,才勉强稳住了灏州防线。
“白都督这番于杨某是救命之恩。蛮子们虽还在外头,到底比之前是稳固许多。”杨九辞连着熬了一个月,面色蜡黄,头发枯干,脸上多了许多裂口,“本是杨某疏忽之过。”
“此番灏州有难,守土本是我将士之责,更不说平日里多承杨刺史照顾,灏州苦寒边远,若非杨刺史,只怕军中也不稳。”白连沙只笑,“赵将军带着神机营同粮草也已到了幽州,想来不日即可增援。”
到底河川边上,冬季封冻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便要从缺口攻进来。中间的神封城还在苦战,若一下守不住只怕灏州也不能完全保住。
尤其是饶乐一带,一旦失守,明后两年北境就全无粮草供给了。
杨九辞勉强撑着点苦笑,只沿着城墙望向外头的荒原。阴云密布,衰草连天,只烈风刀子似的在脸上刮蹭,要将人撕下几层皮来。
“我只怕,他们一早先放细作,还另有他想。”
赵殷带着先行队伍赶了二十多日,才总算在幽州城外落脚。
高南星早和朔州刺史袁渊借调了粮草来支援神机营,一面地安排了人去送些冬衣药材,并遣人换下些民夫,好再往北去。她在幽州守了十余年,虽担着上州刺史的位置,到底边地苦寒,夫侍儿女尽皆留在京城罢了,多年来也是孑然一身,只一小侍跟着伺候。
“辛苦高刺史了。”
高南星一面微微避过了赵殷这一礼,一面沉着声音道:“到底是年节底下,今日才初叁,赵公同将士们才是劳顿。”她说着便下意识叹了口气,“只怕陛下在京中也急。”
“有神机营,想来灏州暂时可稳,陛下应当放心些。”赵殷陪着高南星往中帐里去,“到底年节底下御驾亲征,只怕引得民庶忧惧恐慌。”
“赵公……”高南星十分无奈,“您平素最是小心谨慎的,怎么如今却忘了,五公子还在宫里呢。”她四下环顾一圈见着没人了,才小心地放了帘幕,压低声音道,“您带着人来,不叫陛下出京,这仗到底是胜了好还是不胜的好?在下远在边地都已听闻,朝中早有猜测继后的风声了。”
帘幕厚重,刚好挡下了外头呼呼作响的风声。
“……胜的好。”赵殷沉默了半晌才道,“自然是要想法子退了蛮子去才好。北境不比东南隔海为天险,不若西南树林瘴气,北境一旦破了,中原便如俎上鱼肉,任人宰割。”
高南星身材是剑南女子常见的娇小,微微仰着头去看赵殷,只觉这人下颌胡乱冒出的胡茬格外显眼。都是年过半百,也算是半只脚进了黄土的人了。
“陛下派了您来,未必不曾想到这些。”她自己倒了杯水,又给赵殷倒了一杯,“只是您切莫再拦着陛下亲征了。此话旁人谁都说得,您说不得。”
御驾亲征,自然赢了是天子的功劳,梁国公府无需担忧功高盖主的名头,皇帝也不必在后位外戚中进退两难。
“更何况,宣平侯之事在前,五公子晋封在后。”
一时沉默,只听见外头分发冬衣并年节吃食的嘈杂声。
高南星自饮尽了杯中水,才一拱手退了出去,只留着赵殷一人在中帐里。
塞北的风越是到了这时候越是肃杀,卷着不知从何处裹挟来的草渣沙尘便往人脸上扑,枯干冷硬的,非得撕了人面皮,呼啸得耳尖发麻才肯掠过去。
大楚天子的銮驾伴着亲征的消息一早便声势浩大地传回了北境,连王廷里头喝着烈酒的主子们虽惊得一凛,口中却也忍不得要叱一句:“五十岁的老夜叉竟也能爬得起来!活该冻死她去!”
可惜銮驾是个空銮驾,只京畿道周边几镇兵力跟着御驾壮壮声势罢了,大概是冻不到的。
皇帝本人早先于銮驾到了灏州前线,夜缒前线中帐,倒将杨九辞吓得不轻。
彼时她正同白连沙及军中长史粮官等人商讨如何夺回神封城,帐外便是一声轻响,吓得里头人当先便拔了兵刃出来。待看清来人,才见着是皇帝。
銮驾脚程还没过云州。
“劳烦两位爱卿着人将朕的马牵去喂些水草了。”皇帝皮裘裹身,风帽上还沾了不少雪珠,看来又是偷偷摸摸来的。
杨九辞膝盖一弯便跪了下来:“臣一时忘形,丢了灏州,还请陛下责罚。”
“罚不罚的也总得等事情了了再说,你这颗漂亮的脑袋朕拿来也没什么用。”皇帝淡淡笑道,一手扶了杨九辞起身,“灏州城内不少胡人,总不好都打成了细作。”
“是,臣忧心细作不曾尽排,只封了门户,不叫出城罢了,”杨九辞一见便是几日没合眼了,满眼的红血丝,眼泡肿起,哪还有平日里的美人面相,“目下灏州城虽守住了,神封要塞却还没拿回,是臣贪色失职,还牵累了灏州百姓同定远军将士们。”
“罚不罚的也都是后话了,”皇帝一面招来粮官吩咐几句,一面教身后亲卫解了皮裘去挂上,“当先是连上神封,再退了兵马——可探出来是哪路人么?”
此时却是白连沙拱了手道,“回陛下,原先混进来的细作是早几年便被吞并的图兰部,如今攻打灏州的却是王廷新组的铁甲军。”
皇帝不禁挑了挑眉,随手拔了头上银簪挑亮了烛芯,“铁甲军?不是通泰四十九年便被全歼了么?怎么,他们又组了一支?”
“正是。这支铁甲军是近几年才活跃的,吞并了不少周边部落。”
皇帝微微转了转眼珠,将银簪插回头上去,“是那个第叁王子?朕记得,他爹没什么本事,却生了个好儿子。”
杨九辞闻言便笑,“陛下明鉴,旧唐宫故事多矣。”
“你这人,不想着怎么用兵,倒在此处费神。”皇帝佯怒,只撑了头一面去看后头粮官呈上来的明细,粮草其实所剩无几了。
帐内影影绰绰,火光颤动,带着毡布上的影子也颤动。
“臣不敢。”杨九辞一拱手,留下白连沙一人在旁边摸不着头脑,只能愣愣地看着旁边两个女子一唱一和的。
“臣愚钝,还望陛下明示。”
谁知皇帝只是笑,“白卿莫慌,目下还是以夺回神封城为要,至于这旁的,还需花些气力,打通关节才行。”她指了指粮官呈报的东西,“而今粮草告急,便是省俭也只有一月可守。朔州唯秋季可收粮食,此时只能等关内调运粮草回援,我们需一月内解了这铁甲军。”
皇帝笑眯眯地,说着灏州紧急,面上却丝毫没有军情紧急的意思,还有闲心笑杨九辞憔悴太过,该去洗洗脸。
可惜白连沙仍旧云里雾里,只能以为皇帝是在强乐,“陛下容禀,铁甲军占据神封,若沿着河川往十方湖去,只怕要一举偷取我幽云朔叁州,一月内,如何抵挡呢。”
挡不住,当然挡不住。
杨九辞只笑:“自然是陛下天威圣德,承运降福,破了我灏州危局。”
銮驾莫名其妙在云州境内消失了。
连带着皇帝身边十二禁军营卫同叁镇兵马,集体在云、长、冥叁州交界处消了声息。
天子销声匿迹,本该是被极力隐瞒的消息,没想到这消息却长了翅膀似的,在几州游荡的牧人间疯传,直言天子遇刺,营卫与兵马尽皆流散,只能归往云州刺史处。
圣驾半路失踪,兵马又归入云州。这边灏州正久攻不下,士气低迷,听了这消息反以为大楚的天子要从云州绕行,从背后袭击,一时快报了王廷另派一拨人马直往云州去。
云州府内韩刺史听闻不由大呼冤枉:“我这里哪有什么兵马投奔!”自然这消息也跟着不知哪来的隔墙之耳不胫而走了,一时间倒显得天子带着的兵马遇着什么神人仙境似的,一夕间蒸发了。
过了叁日,銮驾又在云州城外冒了出来,晃晃悠悠过了云州府后,幽州刺史却又接着了銮驾。紧接着,本不在行军路线上的朔州也接着了銮驾,一时间众说纷纭,不知哪一部才是天子辇车,各州连带着云州韩刺史都转了口风,尽皆一口咬死了圣驾亲临,浩浩荡荡地已往灏州去了。
只是不知为何,牧人却传起了叁部銮驾都是空驾,圣人早带着亲兵去见了漠北王廷的要人,将助力此人夺得汗位的消息。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无人摸得着头脑。
“这消息怎么样?”法兰切斯卡笑,一边拉了拉缰绳,让马走得慢些。他一头与汉人截然不同的金发尽皆包进了头巾,再戴上兜鍪,不细看倒也发现不了他的异族人身份。
两匹马行在山脚下,沿着草坡缓缓而行。虽是草坡,到底冬日里清寒肃杀,不过偶有几枝高些的草木,余下的都只匍匐在土坡上,还沾着未曾化尽的残雪。
自御驾兵马分了叁路从云、朔、幽叁州过境,铁甲军明显兵马减少了些,却听着朔州云州连连朝灏州发报,尽是言及分了兵马在他们城下拦截天子的。
“办得不错。”皇帝的脸隐在面具后头,也不显了出来,只能从声线辨别出她带了几分笑意。她只穿着锁子软甲,外头罩着厚皮裘,连兜鍪也隐在风帽底下,“总认灏州一座城打怕他们也无聊,让他们打打云州朔州去。”
“你到底在玩什么啊,灏州不还是没有粮食么。”
“是啊,还是没有,”皇帝仍旧是笑,“之前叫你办的另外一件事办得怎么样了?”她一手抓着缰绳,一手拢了拢风帽,“我们的人没什么事吧?”
“没有……”法兰切斯卡拉长了尾音,很有些无奈的样子。他似乎全不怕冷,衣裳也还是春秋时候的衫子,只多罩了件罩甲罢了,“大秦商队谁会想到是你的人啊,而且漠北的人也是人啊,他们也要吃饭的,不靠商队送东西怎么活。”
忽而,两匹并行的马都跺了跺前蹄,打了几个响鼻。
皇帝同身侧的亲卫对视一眼,拨动马头相互靠近了些,下马隐入草丛。
是人声。
看样子对方已等候多时了。帐篷看着搭起来还不多久,薄薄一层,胡乱盖了些毛毡防风。几人绕在帐周,外头还守着几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守卫。
“若有变要你全做掉,你有多大把握?”
“这么点人,叁息就够了。”妖精只笑,“你总还要出点力。”
“嗤,连我都算上了。”皇帝拿他没办法,正了正面具才牵了马往前去了。
帐中男人等了很有一会儿。
楚国皇帝亲征而来,銮驾却分了叁座,若走灏州倒也罢了,前头铁甲军自然挡着;可若是走云州或朔州边境出关,两路都可能绕至铁甲军后奔袭铁甲军,一时间王廷内不论主战还是主和都很有些忧虑。
到底冬日里缺吃少穿,每回都是这么季节败在楚军手下,尤其是楚国皇帝手下。
“大人,特使到了。”
“已经到了?有几个人?”这男人一时站了起来,跟着报信的亲随便往外迎出去。那叁王子年轻,有领着铁甲军这些年没尝过败绩自然气盛,可他们这些老人都是经历过前头几次溃败的,此时正好借着楚国皇帝的特使说和。
谁要和那么个毛头小子一起葬送了家底去。
“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远远看去,高些的是个男人,并不像旁人似的裹着皮毛,反倒是轻便装束,丝毫不受严冬影响;旁边的人倒是裹得严实,皮裘风帽斗篷一件不落,面上还罩了一张半脸面具,大约便是楚国皇帝的特使了。
“见过两位特使。”男人学着楚国礼节拱手作揖,将两个特使迎入帐中,“在下恭候多时了。”
漠北自连着两回丢城陷地后,王廷中逐渐起了习中原汉话之风,更有甚者还将楚人习俗文艺等尽皆学去,连在王廷内也打扮得与汉人一般无二。
自然了,在楚人听来,不过东施效颦,贻笑大方罢了。
“劳烦大人等候。”皇帝点头致意,只跟着人进帐里去,后头自有亲卫随在两步之后,“漠北苦寒,是辛苦大人了。”她先端出一副半笑不笑的神情来,也不说坐下,只抄着手等漠北来使先起这个话头。
谁知这男人当先摒退了帐中其余人等,压低了声音道:“实不相瞒,在下是旧四王子的人。”
他本想着抛出这句话,对面总须得落下些表示,可一见眼前这个特使仍旧是一副半笑不笑的样子,两手只抄在袖中,一丝惊奇也无,不由有些弱了气势去,“新王主战,大肆清除求和派,还请皇帝陛下不要将我们与新王混为一谈。”
“求和的羽信,杨刺史已收到了,我正是来全权处理此事的。”皇帝这才回了一句,不痛不痒地,“阁下还有何见教?”她甚至轻轻呼出一口气,看着面前飘出一团白雾。
灏州守了叁十多日久攻不下,虽暂取了神封城,却也一直没有进一步的进展。王廷见久久无法占据上风,又是大楚皇帝开了銮驾亲征而来,自然便要忆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溃败,一时间求和之风大行其道。
新汗虽是坚定的主战派,却也无法一时杀尽求和派,这才让这几个被打压陷害了年余的求和派塞了人出来,夜送和谈书,请求单独与大楚和谈。
“不敢。”男人很有些憋屈,早听闻中原不少女人当权,连皇帝都是女人,可没想到这么个来单刀赴会的皇帝特使也是个女人。前线交战派女人出使,这女人还不把人放在眼里,“赐教不敢当,只是我们王子有意求和,还望皇帝陛下赐福。”
面具下透出的两只眼珠子略微转了转,才将眼光落在了毕恭毕敬的男人身上:“你们王子求和,王廷可还没有求和的意思。陛下只知灏州城下铁甲军乃是你们漠北人,无端地来抢掠我大楚的子民,掠我大楚的城池。”
男人闻言心下反略松了口气:“我们王子只需陛下的口信,只要皇帝陛下愿意赐福,我们定当献上让皇帝陛下满意的礼物以表心意。”
皇帝在面具底下略微挑眉,面上跟着便笑了一声:“这礼物满意与否总还是要看合不合陛下的喜好,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自然,自然,我们保证一定让皇帝陛下满意。”男人陪着笑道,“只要皇帝陛下愿意支持我们王子,我们定献上王廷最亮的明珠。”
怎么还要花钱帮他们内部夺位了。皇帝略略勾起了唇,将手背去后背,些微露出腰间的剑柄,“既是要我大楚花费银钱,王子可有何定金否?”
“请皇帝陛下放心,我们一定按时送上定金,向陛下表达我们的诚意。”男人微微弯腰陪笑,说着便从衣襟里掏出一枚金印,“这是我们王子的金印,暂且交予特使大人,算是我们求和的诚意。”
皇帝将东西放在手里把玩了片刻才松了口,“金印为信,分量倒也足了。本使回城后自会如实禀报陛下,陛下自会在合适的时候帮你们王子一把。”她顿了顿,才想起来似的道,“只是若灏州失守,陛下也只能当作今日无事发生了。”
“自然,自然,铁甲军只交给我们王子便是,日后定然献给陛下处置。”
皇帝不置可否,只笑:“说了这么些,到底如何支持你们王子还是陛下说了算的,只不过我代陛下承诺,只要陛下看到你们王子的诚意,这份情便一定会奉还。”
“如此,在下便先谢过皇帝陛下赐福了。”
“喂,他们说要出手你就信啊?”两匹马缓缓往灏州方向回去,见不着先前的帐子了法兰切斯卡才总算一吐为快。
“信不信的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现在知道了他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就好办了。”皇帝随手把玩着先前的金印,心情颇佳,“銮驾分了叁路往前线去,又不是盯着铁甲军去的。”
“不是?”这下轮着妖精瞪眼了,“你不是要救灏州?”
“是啊,但救灏州也不是非得先破那铁甲军嘛。”皇帝两只脚蹬着马镫晃晃悠悠的,有一下没一下地压着马背,“不如一劳永逸……”她话还没说完便迅速拨转了马头,隐到山背坡去。
有人。
一整队的带甲骑兵。
法兰切斯卡也早跟着隐匿了起来,压低了声音道:“看着和神封的那些差不多……”
“应该就是铁甲军。”皇帝只盯着骑兵看。这一队人数不少,轻装上阵,没什么重武器,应当是侦查用的。
“怎么办。”
“先等等,等他们走过了我们再走。”到底只两个人,便是这妖精一骑当千也未必见得能兼顾。
过了好半晌,两人才从坡后起来,驾了马往灏州方向去。
还没走出几步,便有箭矢落了下来。皇帝心下一凛,策马躲开飞箭。身侧亲卫反应更快,早拔了兵刃将流箭全挡了开去,一脚踢在皇帝马屁股上,激得马撒开蹄子便往前冲去。
有埋伏。想来先前那一处便已被发现了,只是对方沉住气,硬是等了这么久才发难。
很冷静嘛。皇帝接着又飞奔对方不易命中,视线往四下一扫,这几枝箭原来是马上射出,弓箭手已当先见人飞奔出去,来不及再射,已弃了弓箭策马包抄而来。
只可惜没有长枪。皇帝扭头看了看亲卫,妖精已经挥鞭跟了过来。没有长枪马战不利,还是想法子跑出去才好。她左手握住马缰,右手展开马鞭,将身子尽量伏低了避开矛尖,一展马鞭抽在马臀上,借着疾冲的劲头松开缰绳,拔剑砍往最近的马头。
对方为了轻便作战,只有人带甲,马却是裸着的,这一下砍过去,自然胯下坐骑便废了,一下滚落到草坡上。
“王子!”
哦?皇帝挑眉,随手将剑丢在箭袋里,抽了一支箭便回身射出。
那边人才爬了起来,抓着另一人飞身上马,不料一箭飞来,将将好穿过肩头,又将人打到地上。
“法兰切斯卡!”皇帝叫着妖精名字,一面勒转了马头攻回去,半身挂在马上,抽了袋中长剑劈砍马腹,惊得马群几乎失控。
妖精早知道皇帝意思,从后头跟上来,从马背上纵身跃去敌兵身后,也不多话,只将人摔下去,再以短刃刺进马臀,惊了马匹,才跳回自己马上。
一时惊马乱走,反踏死了几个落马之人。
皇帝正好迅速射出几箭,拦了几个要去救那最初落马之人的敌兵,心一横,伏低身子冲回乱马群中,俯身抓了人上马便拨转方向奔逃出去,只留着法兰切斯卡断后。
“别乱动。”皇帝毫不留情,一马鞭甩在俘虏身上,只可惜冬日里衣裳甲胄都厚实,看来没怎么痛到实处,只有再一鞭甩给马臀,先策马逃出去为妙。
没想到这人被倒扣在马背上也没忘了挣扎,竟然偏过头一口咬在皇帝手腕上,一下激得皇帝松了缰绳,又是连着几鞭子甩在人身上:“你属狗的?!”
“……”前头这人也不回话,只手慢慢摸上后腰,意图去抽腰间短刃。
皇帝一眼扫着,又是一鞭子抽下去,“你想都别想。”她一面松了缰绳,自己抽了面前人腰间短匕来丢进箭袋,又是提着领子将人在马背上挪正了,见他还不放松,脚上便松了马镫,冲着前人脚脖子踹上去,“老实点。”
“……”这人一言不发,身上倒是老实了些。
还没跑多远,他却趁着皇帝调整方向间隙一下跃起,双掌拍在马颈上,惊了马,抢了半边缰绳同皇帝扭打起来。却没想到此时马正行过山脊,一时平衡不稳,竟拽着皇帝连人带马一起滚下了陡坡,冲碎了河面冰层,一下落入水中。
————————————————————
阿瑶:骂骂咧咧退出战场
哦,毕竟是女主,没事的啦,她有玛丽苏光环(bushi)
最近在思考一些奇怪的问题,比如男女的力量差别到底是基因选择的结果还是必然结果?想了想应该都有。女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因为分工不再在体力劳动中占据主流,从而在食物分配上也慢慢减少,但另一方面,女性没有睾酮分泌增肌确实更慢上限也更低,想想应该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吧。
不过我想日常人类活动需要的力量程度女性应该也没有“必然达不到”一说,不然农村里干了一辈子体力农活的阿姨辈奶奶辈,也没说干不了(力气还很大,比起我这种弱鸡子来说称得上孔武有力了),当然了,比起男性来确实还是吃力一些。就好比流浪猫都是母猫管生管养,母猫还是骨架比公猫小一点,但是母猫普遍比公猫凶多了(也比公猫会撒娇讨食哈哈哈,主打一个能屈能伸),该抢的地盘吃的那是一个不落一点不少,我们家几只小猫咪就属最小的闺女最凶,打不过几个哥哥也要硬打,搞得哥哥们都绕着她走x
兄弟阋墙
同类推荐:
【快穿】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她的腰(死对头高h)、
窑子开张了、
草莓印、
辣妻束手就擒、
情色人间(脑洞向,粗口肉短篇)、
人类消失之后(nph人外)、
不小心和储备粮搞在一起了(西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