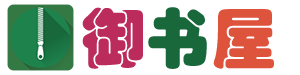那人是擎着一把伞的,伞下也没有别的人,但就是湿了那么半边衣裳。我看了一会儿,发现问题出在他举伞的姿势上。
我以为伞可以是一件武器,它以庇护为名,却借助着雨的力量达到收束人的效果。人们在伞下时,多多少少总有些缩手缩脚的。但此人不同啊——
这人举着伞却完全不用伞,好像不知道举伞是为了挡雨似的,像擎着一杆旗子似的立在船头的春雨里,这种不为外物所动的超然,啧啧,真是不同凡响。
也是真的有病。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病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光是这举伞的德性,我这辈子就不是第一回 见了。
前一个这么用伞的人,我心血来潮时操闲心,问过他:“庄珩啊,你这伞撑啥呢?”
那人看了我一眼,说:“你看这伞。”
我就看那伞。
他指了指伞柄,很超然,很理所当然:“这棍子杵在中间,怎么撑都是半边。是以自有伞以来,伞就是要两个人一起用的。”
我听傻了,看看他伞下那空落落的大半边,问:“那你这是给谁撑着呢?人呢?”
那人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说:“死了。”
第3章 再会
庄珩这个人,现今我只记得三件事了。其一是此人伞撑得不伦不类;其二,这人是周蕴先生的关门弟子,学问一流,性子却很古怪;其三,此人生平好友无多,傅桓是其中一个,我不是。
庄珩人情淡漠,我从前与他没有什么交往,若说与我之间有什么联系,便只有傅桓能说上一说了。
傅桓广交游,与庄珩是好友,最开始的时候,与我也是。那时梁州满城绿柳,满楼红袖,鲜衣怒马过斜桥,亦曾是人间第一流……那样的好风光、好时节,光是想想,都像是这漫长阴雨天中破开天穹的一道光。
“哎……”
想到那后来的事,我又感慨地在蒙蒙细雨里叹了口气。
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了。如今世上已经没有我,没有他傅桓,当然也没有庄珩。日子这么一朝一朝地过去,折戟沉沙,铁也销了。
哎呀,要了命了。
看来做鬼跟做人也没什么不同,做的时间久了,免不了要生出一番老气横秋虚无缥缈的感慨——这才是隔了一片雨雾望见湿了半边的衣裳,就这么顺藤摸瓜地想了一大串,我要是真的鬼生不幸,当真在这里见了故人,或是黄泉路上不小心打了照面,这也是很有可能的,那要如何?傅桓也好,庄珩也罢,都已经是些不能再见的人。
我在这苦水河里泡了百余年,世事都变了几变了,怨愤亦早已散尽,待我这一袋功德存满,一碗孟婆牌黄汤下肚,来世不再做人,总就免去了相对难堪的烦恼。
想到这里,有了些盼头。
我在水面上冒头瞥了一眼,那情状虽然眼熟,却与我没有什么相关,便缩回脑袋依旧沉回水里。
因此便没有看到那身影有所察觉地回过头来,那一身湿透了好似青苔层叠的衣衫之上,一张熟悉的脸。
春山春水溶在眼里,那双如玉的眼眸也成了深浓的墨绿色。
他静静望着水面下悠游游走的一尾青鲤,望着在那款摆的鱼尾之后,一条若隐若现的银白色蛟尾。
东湖边上的小山坳,水汽丰沛的山谷,青绿色的阴雨天。四野无人,舟行河上,岸边的野柳、野杏、野李纷杂而过,隔着层层涟漪的河面,一人一鬼。
在规律而安定的摇桨声里,好似数千年光阴都虚掷了,除了阴阳相隔之外,一切概如当初。
他想起来,上一世梁吟被押解离京的时候身败名裂,去送的人寥寥。
新政门外,也是一个春日。
那日天气晴暖,梁吟拖着铁链,与来人在槐下送别。日光穿过枝叶淋漓而下,落在他身上好似波光跃动,一张苍白的脸像沉在水底,神情捉摸不定,脸上似有笑,又似没有。
简短道过别,便转身去了,春阳下瘦嶙嶙的一片脊背。戴着镣铐的手抬起来,背着他们遥遥一晃:“再会。”
他们终于又再会了。
第4章 无饵钩
顾名思义,杏花渡渡口有几棵杏花,早春的时候在蒙蒙细雨里开成灼灼一片云霞。但杏花花期太短,下一场雨,花瓣便凋了,通通落到河里。
苦水河就成了一条白河。
我站在岸边,对着白河吟那位亡国君的词:“落花流水春去也。”
船从河中驶过去,老船夫的桨破开雪白花被,露出翡翠般幽绿的河水。河底的鲤鱼浮上来,无声无息叼下去一片花瓣。
我忧愁的感慨散在雨雾里。神鬼不识人间事,没人理我。
哎,我又寂寞起来了。
寂寞的时候我就到山谷里的土地庙去。土地公是他们神界的七品芝麻官,我如今虽做了鬼,死之前却也当过人间的三品大员,谁官大谁官小,还真说不好。
土地公占便宜,叫我“梁老弟”。
其实按土地公的说法,我这湖投得不值当。他说我出身好,我爹是个好官,我也是个好官,虽然下场凄惨,但原本积了不少功德,如果熬到寿终正寝,可在天界捞个小官当当,这一投湖,自毁其身,正犯了人间的忌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以功德全销,连根毛都捞不着了。
第3页
同类推荐:
因为手抖就全点美貌值了[无限]、
麻衣神算子、
楼前无雪、
阴差阳做、
百合绽放、
宅师笔记、
人间生存办事处、
租鬼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