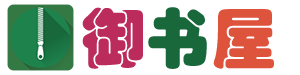我要等到莎莎明白谅解的那一天。
会等很久吗?还是永远不会到来?
年三十
我不知道东霖那晚是几时离开的,因为后来我也站累了,靠着门,我也坐了下来。他在门外,我在门里,隔着一扇门,背靠着背,静静地坐着,谁也不出声。
几乎一整夜。
接近天亮的时候,我打开了门,门外已没有人。
他应该知道我一直在门里默默地陪着他吧。
他肯定是知道的,我想。
第二天,我等着莎莎给我打电话,按东霖的说法,他又和她分了手,那么,她一定会来找我,会痛哭着对我说,东霖又不要她了。
但我却没有等到她的电话。
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已是大年夜,我仍然没有等到她的电话。
这不正常。
照常理,我应该当天或第二天就接到她的哭诉电话,但现在已是第三天了。
可我也没有勇气先给她打电话。那样,似乎有嫌疑,仿佛即使她不告诉我,我也会了解她的一切。我知道自己是做贼心虚。
我只能等着,假装自己是身外人,不知道她和东霖之间发生的任何事,除非她来告诉我。
接不到她的电话,我隐隐的有了恐惧,生出了许多猜想。莎莎是不是察觉了什么,然后是不是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我要失去这个朋友了。
东霖也没音讯了。没有电话,也不来找我。
我不觉得奇怪。
和莎莎彻底的分手,对他来说,也是断腕之痛吧。他也需要时间来治愈伤口,不是马上就能面对我的。
年三十,除夕,中国人最重要的团圆日子,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几乎每年都是这样孤单的度过的。
商场在这个日子照例请不了假,越是大节日,商场越忙,所以我去不了上海,也回不了老家,只能守着A市这座空城。这一天,对我来说,A市就是一座空城。
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却犹如身处孤岛。
不会有人和我吃团年饭。只有一室孤寂。
谢丰会在这个日子记得我,他从没忘记过。但他也从来都抽不出身。他是家里的独子,他还有心蕾。心蕾也是外地人,没有了他,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所以他总是给我打很多的电话,从晚上五六点开始,隔一两个小时就来个电话,不厌其烦。问我几时下班,有没有买菜,在不在看春节联欢晚会,直到我不耐烦的再不接他的电话。
今年也是。
五点多的时候我开始接他的电话,接了两个,我就对他说:“谢丰,不要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在记挂我,我很了解。
他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就真的没再打了。
和东霖在一起两年,两个大年夜,他也是赶回家里去陪父母。他也是独子。他老家就在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地区市,驱车来回五六个小时。他都是除夕的下午走,走之前会给我来个电话,只有两句话:“我走了,你自己好好过年”。
第一年他在大年初四才回的A市,我接到他电话的时候,还在上班。何丽她们照例把很多班推给了我,因为就我最空闲,不用走东家串西家。于是我连着加班,直到生病,却还在上班。
东霖那天难得的来商场接我下班,其实他也是刚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赶回的A市。
在地下停车场,我找到他的车,坐进去就闭上眼睛想睡觉。他立即觉察出反常,抬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你在发烧!”说完他就直接开车带我去了医院。
在注射室,他陪着我做皮试,看着我手腕上的皮肤鼓起老大一个包,当时就问护士药水是不是打多了。
那个护士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本来还对他和颜悦色的,听了他的问话,立即丢给他一个白眼:“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给她打?”噎的他说不出话来。
我头昏昏的,但还是忍不住“嗤嗤”的笑。
他托着我手腕,把它平平的放在手心里,皱着眉看着我笑,脸上有丝难堪的窘迫。
就觉得他掌心热热的,一整条手腕都滚烫了起来。
后来在输液室,一圈圈的椅子,很多的病人,周围几个竟然都是过年吃坏了肚子的人。我和他在个角落坐着,我还是头昏,人绵软无力,他就把我揽在了怀里。
医院的椅子都是单座的,我和他之间横着个扶手,硬硬的硌着我腰,我却在他怀里很快的睡着了。
醒过来时点滴已经打完了,针不知几时抽走的,东霖捏着我手,大拇指紧紧地按着棉球,上面渗着一点点血。
他看我睁开眼,对我说着:“你的血小板太少了,抽个针头都出这么多血。”
我只望住他笑,感觉头顶白白的日光灯都像太阳似的。
那是仅有的一次看见东霖对我流露出明显的关怀,觉的他虽然不爱我,但还是喜欢我的。但也就那一次,以后再没见过他那种样子。
我也再没在他面前生过病。
第二年的春节他回来的很早,年初二上午就回了A市,我也还是在上班,接到他电话:“我到家了,下午我来接你下班吧”
我一愣:“不用了,我自己过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他又要到年初四才能回。
他接着说了一句:“你还好吧。”
第42页
同类推荐:
【快穿】欢迎来到欲望世界、
爱欲如潮(1v1H)、
她的腰(死对头高h)、
窑子开张了、
草莓印、
辣妻束手就擒、
情色人间(脑洞向,粗口肉短篇)、
人类消失之后(nph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