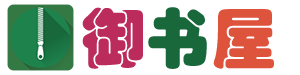她对他是明显可见的敷衍,或许她其实是在竭力显得没那么敷衍,然而心血却已经被耗干了,便是做戏也不会做。
但他不介意,草原上熬鹰的时候熬到最后,两人往往都是精疲力尽,只要猎人将鹰熬到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会发自内心地顺从他、依恋他。
如今的再怎么别扭也是暂时的,只要调弄好她的倔性子,将来两个人照旧是和睦美满。
“只是今日侍中会来宫中见朕,想来也该叫太后与秦王见一见,行拜师礼。”萧明稷笑着理了理常服,“人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朕想着也不用太过正式,叫秦王来磕个头也就算了。”
郑玉磬心里一惊,她对老师一向是极为尊重的,便是当年窦侍中教导元柏,她都是四时八节的礼物不断,即便是对这位新侍中起了防备,但依旧备了一份厚厚的见面礼,哪里能不重视,这么马虎,还让人在外面等着呢?
不过萧明稷大约本身也没存什么好心思,哪里肯真正为元柏认认真真地拜师?
“皇帝和宰相想来还有话要说,我先回去换一身衣裳,等一会儿携秦王过来谢恩叩头,”郑玉磬总不好刚与他私通过,便穿着这样一身衣物来见侍中,“国家大事,我一个深宫女子不该在场,外面没有人知道我在皇帝上朝议政的这里,难道不好么?”
她起身欲走,却被萧明稷握住了手。
“何必这样麻烦,万福,叫人将秦王带来,”萧明稷今日倒是难得的和颜悦色,他看向郑玉磬承恩过后妩媚的模样,浅浅一笑:“为太后另设一处坐席,让秦侍中进来吧。”
皇帝也还没来得及换下朝服,索性又叫人取了冠冕佩戴,他的神情间已经没有了那等不正经的风流神色,一双含威的眼眸被十二玉旒挡住,正式威严,叫人不敢直视。
骤然从萧明稷口中听到这个姓氏时,郑玉磬的内心波动了些许,然而天下重名之人都不在少数,重姓的便只会更多,就连上皇当年也是指了几个秦姓的进士。
皇帝身侧的侍女将她的头发打理妥帖,郑玉磬在外臣面前到底还是有几分尊严的,她额头上的青痕已经好了,倒也能够见人。
“先宣人进来吧,”萧明稷的面色没什么不好,甚至称得上是愉悦,“他身子骨一向不太好,别在外面冻出什么事情来。”
大殿的正门缓缓开启,那缓慢绵长的“吱呀”声带来了一缕冬日的阳光,仿佛乌云压抑得久了,逐渐有了破晓的迹象。
一双朝靴踏在阳光洒落的大殿朱红色织锦地毯上,那个清瘦却不减风骨的男子逐光而来,仿佛那人身上的紫色官服周边,都淡淡拢了一层细密明亮的光。
郑玉磬起初还不大适应阳光照进来,然而当她的眼睛逐渐适应之后,却无意识地半张了檀口。
多年不见,那个藏在她记忆里的身影已经逐渐模糊,但是当那个执了象牙笏板,身穿紫色朝服的男子再一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那心底的印象瞬间便清晰了起来。
他曾经见过她作为新嫁妇的为难,但是他再怎么名声满城,终究还是要守孝道,而且官职不高,也没有办法护住她。
所作的轻轻替她揉捏站累了的小腿,用药膏涂抹她被汤汁热油烫红了的手背,说等他将来满身朱紫,一定会叫她不那么辛苦于柴米油盐的平淡,舒服地过贵夫人的日子。
将来的秦夫人会是一品诰命,有天底下最华丽的衣衫和首饰,叫旁的诰命夫人艳羡她。
她不知道印象里似乎早已经去世许多年头的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但是如今两人确实实现了当年的憧憬,只是物是人非,竟然是谁也不高兴。
青年为宰做辅的他依旧萧疏淡远,却不见少年意气风发,而高居凤位的她也失去了原有的活泼明媚。
而秦君宜入殿的那一刻,自然也望见了正向他看来的郑玉磬。
她已经没有当年作为贵妃入宫时的丰腴,反而是消瘦了许多,哪怕容貌出落得更加艳丽,但是眼神中的落寞与见到他那一瞬间的惊喜依旧叫人觉出十分的可怜。
想来音音这些年在宫里也未必好过。
他神色微怔,然而旋即向萧明稷与她请安。
“臣秦君宜拜见圣人、太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他的中气不足,但是吐字依旧清晰有力,刚要跪下去的时候却被萧明稷唤了起身,“既然都是旧相识,便不必行大礼了,让人搬胡榻过来。”
皇帝这话若是对潜邸旧部来说自然是亲近勉励的,然而依照他们几个的关系听起来,却是格外的讽刺。
对于郑玉磬来说,这一点其实是毋庸置疑,她袍袖下的手被身侧的帝王用力攥住,那种触觉提醒她回过神来。
今上身子微微向太后的方向侧去,冠顶十二玉旒微微晃动,似乎含笑要与她演出一副母慈子孝来,然而实际上却牢牢握住她的手,笑容清浅,云淡风轻。
“太后若是再瞧秦侍中一眼,今夜送到长信宫的必然是秦侍中的项上人头。”
萧明稷心底怒意滔天,郑玉磬别以为他没有瞧见她刚看见秦君宜时的口型与眼中盈盈泪意。
美人惊讶至极时真情流露,分明无声落泪,唤了一声“郎君”。
他便是在最卑微的时候,也不见郑玉磬肯真心这般唤他,然而秦君宜不过是露一个面,便拥有了他轻易不能拥有的东西。
这么多年过去了,连放妻书也写了,可是郑玉磬心底,念念不忘的人还是他。
不过就算是如此,秦君宜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妻子柔顺地依偎在自己怀里,而他的孩子,却对着别人叫父皇,心心念念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阿爷。
而郑玉磬却也从那不可置信的狂喜中回过神来,她如枯井无波一般的心底骤然升起惊涛骇浪,然而正是这份震惊,叫她生出不知道多少个念头,克制住了自己的双手,面上逐渐平静了下来。
“皇帝这说的是什么话,”郑玉磬顾盼间眼波流光,甚至还反握住了他的手,苦涩一笑,轻轻道:“过去的一切早便过去了,只是从前叫的习惯,我原以为你早便将他杀了,没想到还留他的性命到如今,颇有几分吃惊。”
“我如今这样,不看开又如何能行,不过我倒是想知道,皇帝,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压低了声音与他窃窃私语,难以置信中透露着笑意:“不是恨得他要死,居然还会给他封官?”
她是真的不敢相信,玉阶之下站着的居然当真是自己曾经的夫君,萧明稷居然会留下他的性命,而不是借上皇的手杀了他,实在是叫人吃惊。
萧明稷已经习惯了每回她那般木讷无趣的顺从又或者令人更加发怒的反抗,郑玉磬那惊喜一瞬之后的释然与平静反而出乎他的意料,他慢慢松开了郑玉磬的手,甚至还轻拍了拍。
她肯这样,无疑是极好的。
“好了音音,这有什么好笑的,等朕回去再和你说。”
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事或许有些不符合常人所想,但是当他听见郑玉磬似乎是出自真心地觉得好笑时,他反而受到了一些感染,一点也不生气,甚至也有了些真心的笑意,“你怎么这样,在人前一点面子也不知道给朕留?”
皇帝与太后说笑了片刻,便去询问秦君宜一路上的风土人情与洛阳城里的事情。
萧明稷对政局掌控欲极强,对自己的旧部在政事上严厉,平日里却偏心,他询问得极为仔细,且一边问一边留心郑玉磬的神情,然而秦君宜坐在帝王下首,也是对答如流,丝毫不怯,显然是成竹在胸,也不担心皇帝会有所盘问。
郑玉磬在皇帝谈论政事的时候自然是闭口不言,只是她似乎无聊得紧,只能垂首呆呆看着自己衣裳的绣纹,似乎想研究明白那是怎么织成的,只是偶尔留神到皇帝的目光,无奈地将头侧到另一边去。
秦君宜这些年于情爱上淡泊,反而更多了些沧桑历练,更不曾失礼去看太后,叫人放心得很。
如今这场安排的结果虽然说是让人满意,但是反而显得天子太刻意了一些。
她听得到秦君宜的声音,明明心情激荡,但是却不敢抬头看他一眼,生怕那一眼就已经叫人肝肠寸断,她就再也装不下去了。
仿佛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而坐在底下的那人,平视玉阶,面对帝王侃侃而谈的神态自若之下,却并不比她好上半分。
他明明知道,他们两个已经不再是夫妻了,然而见她金装玉裹,却憔悴如斯,心中的怒气几乎不可遏制。
贵妃被重新送到道观里面,其中细节内情,他隔了一个月也便知道了,便是送信来的周王府下人有心隐瞒,他大致也能推断得八||九不离十。
而音音所生的那个孩子……他每每午夜梦回,都生出过不敢说出口的妄想。
他们父子从他的身边把他的妻子夺走,讥讽他没有资格得到如此美丽的解语花,然而却也没有真心对待过郑玉磬,反而叫她日渐憔悴。
郑玉磬在一旁听着,已经听出来了些端倪,她并不蠢笨,从前上皇甚至教过她这些,怕孤儿寡母遭人欺负糊弄,她却只能干着急。
她的丈夫,在洛阳城、或者说是在如今皇帝的身边亲信中,已经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后来萧明稷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突厥可汗长子的事情上,而在这其中,秦君宜似乎参与得也不算少。
御前的内侍躬身进来,禀报太后身边的宫人已经领了秦王过来了。
秦王今日穿了一身正式些的小朝服,身后有内侍跟随,托盘上摆放的是沉甸甸的谢师礼,他向皇兄与母后行了礼,而后等待人介绍在他面前坐着的这位身穿紫色官袍的秦侍中。
“明弘,快过来,这位是你的新老师,也是你皇兄新下旨晋封的秦侍中。”
郑玉磬竭力柔和了音色,先是看了一眼萧明稷,而后得他同意才从坐榻处起身,拽起萧明弘的手,温言对秦君宜道:“这是你皇兄的一番苦心,一会儿你再拜一拜圣人,记住了吗?”
萧明稷平素虽然不喜欢她花太多的心思在萧明弘身上的,可是明面上依旧十分厚待这个唯一的弟弟,并且郑玉磬在大面上能够以他为先,那就已经足够了,也同样温和地与萧明弘道:“元柏看起来近来又胖了许多,可见清宁宫的厨子伺候用心。”
秦君宜定定看着那个孩子,受了这位皇子半礼,侧身回避,或许是他的错觉,那个孩子的眉眼虽然与郑玉磬十分相似……但是隐隐约约,又能看出些他的轮廓。
或许这不过是妄念,恐怕连如今的太后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子嗣。
只是当着皇帝的面,秦君宜便是心中有千般思量,也只好考问些正常的课业,他本身人便俊秀年轻,说出来的话自然与窦侍中那样古板刚正的老学究不同。
加之存了隐秘的心思,对待这样一个小孩子,便是不用提前备课,也格外存了宽容的心思,将几段文字剖析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元柏本来是得过宁越的嘱咐,不必对新的老师抱有太多的期待,然而当他和这位秦侍中见面说话以后,便觉得他实在是阅历丰富,又学识宽广,即便是稍微病弱一些,说久了便要停下来歇一歇,可是仰头看着他那张脸,他莫名就觉得很是亲近。
最后还是萧明稷瞧着这逐渐温馨起来的画面略有些不悦,与郑玉磬说笑道:“太后若是无事,不妨先回长信宫去瞧一瞧可还称心如意,朕与秦侍中尚且有话要说。”
回去的路上,元柏还有些未褪的兴奋,他本来就年纪幼小,近来又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今日突然碰上那么一位合心意的老师,心里欢喜得不行,话多得像是一只麻雀,和阿娘又重复了一遍今日发生的事情。
郑玉磬瞧着他这般快活,心中百味交杂,只是为他抚平幼儿梳不成髻的碎发,虽说眼中依旧常含泪水,可眼神里除了忧愁,难得明亮了许多。
她从未奢求过这样一天,原本惨死的郎君竟然能亲眼看见他们两人的骨血,只是有萧明稷在侧,她纵使是有满腹的话语,也没有办法将真心话交付。
“阿娘也为我高兴吗?”
郑玉磬点了点头,她心里存了许多疑问,可是如今充盈内心的却更多是与故人重逢的喜悦与一些大逆不道的念头,暂且将那些愁思冲淡了,她含笑道:“自然如此,元柏高兴,阿娘也高兴。”
元柏坐在阿娘半卧床榻的侧边,见到宁掌事的神色并不算好,想到阿娘的处境,忽然又叹了一口气,像是个小大人似的说道:“可是阿娘,我不能同秦侍中好好学的。”
那位皇兄与他的阿爷几乎是两个极端反例,自己好好学,就会叫那位皇兄不痛快,他不痛快,阿娘与自己都不得开心。
长信宫经过精心布置,只剩下了一点尾没有收,但是明面上他们同上皇住在了一起,可是私底下还是不能相见,御林军轮班值守,不允许太后越界,便是再迟钝的人也能觉察到不对。
然而郑玉磬虽说听他这般懂事的时候面上略带了些忧愁,可是末了却莞尔一笑,“你想学就学吧,秦侍中是良师,不必有所顾忌,只怕你学的不好,反倒可能惹他生气。”
她心中似乎有一块大石头即将落地,不过这松懈的前一瞬,却又生出无数个疯狂的念头,那些念头本来已经再无可能,但是在见到郎君之后,又如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萌芽,叫她平添了一股新的力量,一扫原本的行将就木。
“真的吗,阿娘?”元柏有些喜出望外,伸出自己的胖乎乎的小手去勾她颈项,伏在郑玉磬的怀里待了一会儿,而后却又有些疑惑地抬头:“阿娘为什么这般笃定,难道您与秦侍中之前认识么?”
“元柏听说过什么是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吗?”郑玉磬闻言迟疑片刻,却避而不答,伸手去探他颈后温度,“阿娘只是有一种直觉,觉得秦侍中或许该是一个素日温和的男子,说不定比你阿爷待你还好些。”
第72章 晋江文学城独发
“音音, 这回你总该满意的。”
萧明稷一边在看秦君宜递上来的奏疏,一边漫不经心地在郑玉磬光洁的肩头处流连,他这些日子刻意待她不好,怎能看不出来, 音音不高兴极了, 也怨恨他到了极点。
他虽然一边想要像是熬鹰那样熬她, 把她所有的不恭顺都磨掉, 叫她意识到自己从前待她是有多好,但一边又舍不得她逐渐死气沉沉, 终究狠不下心,暗地里想法子哄她。
如今他贵为天子,有能力也有心给她最好的一切, 送她最精巧的首饰、最上等的补品,连两人燕好的次数都减少了,两三日才尽兴一次,更多的只是叫她待在身边陪伴理政,偶尔情难自禁的时候才宽衣抚触一番,尝一点荤也就撂开手了。
他让江闻怀隔几日便要请一次脉,恨不得将她立刻便调养得白白胖胖起来, 只是都没什么用处,他的音音还是不高兴。
江闻怀被皇帝质疑了几次医术,才战战兢兢对他道, 哀莫大于心死, 太后如今心情不畅, 不肯用膳,便是用了也会恶心,这样只出不进, 长久下去,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用处,除非叫她重新愉悦起来,病自然也就好了。
她总是这样呆呆的,确实原先对待他的别扭性子都磨没了,温顺了许多,只是也没有什么求生的意识了,叫他有了几分害怕。
然而她狠不下心去死,却也是早便不想活了,只是知道反抗不了,也不花力气去反抗,但瞧不见什么盼头,不会主动逢迎他,只是一日日地枯萎下去。
熬鹰原本就是这样,有一些起初刚烈反抗的,会用沾满血的喙一下下去啄铁链,然而到了饥肠辘辘、无力反抗的那一刻到底还是会顺从,从此认猎人为主,而有一些即便平日里看起来柔弱的,却被活生生熬死了。
他想发怒,可是瞧见她单薄的身子又不忍心,只是装作瞧不见,想着她在父亲后宫里的时候原本就没受过什么委屈,如今自己这些手段虽然也没有多狠,可是她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罪,肯定还是打击坏了。
直到他最终还是妥协了几分,下旨意让秦君宜回来,郑玉磬才看着眼中明亮了些许,她每日肯和他多说两句话,也会偶尔笑笑,饭菜要是遇上合意的也能多用半碗。
前几天甚至松口,答应去和他除夕一块登临五凤楼接受臣民朝拜,上元夜一起赏火树银花。
这一步看起来倒是走对了,音音确实有了些求生的心思,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不过相比于秦君宜的感受而言,他还是更在乎郑玉磬对他的态度,虽然他们关系的缓和里有秦君宜的因素在,但好歹音音身子好了一些,他私底下生一生气,面上倒也能忍住。
金屋囚 第72节
同类推荐:
偷奸御妹(高h)、
为所欲为(H)、
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
肉文女主养成日志[快穿系统NPH]、
娇宠无边(高h父女)、
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
彩虹的尽头(西幻 1V1)、
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