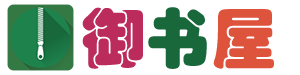刚上中学,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
那是新生报道的第一天,我坐在第一排,什么人都不认识。老师让排头的同学收什么钱,我便挨个收下去,在收到第五排的时候,抬头瞥到了她的脸。当时我失了态,怔怔地看着她,钱都忘了收。
这是十年零四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我还记得那么清楚。
那时喜欢闷闷的。同学们都很坏,有人因为我在课堂上抢答了几个有难度的问题,就愤愤地看不起我。老师们也很坏,有些问题本来是不想让学生答,如果他们有这个想法,一定有个询问的表情,语调上也有变化,会看脸色的同学立刻把书上的句子七嘴八舌地念出来,这样大家都很满意。那时候课堂上的规矩,我不懂,总是打破它,於是老师也很讨厌我。他们联合起来,把我弄到了最后一排。
作为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是很容易学坏的。中国中小学的排座位,原则上按照成绩来,个别家长打过招呼送过礼的另算,像我这样的也另算。於是我和坏孩子中的坏孩子排在了一起,有人陪我说悄悄话,就没心思抢答老师们准备自己回答的问题了。第一次考试,比入学成绩下降了五十名。我回家挨了打,父母着急地给某某人送了礼,班主任很高兴。
再不久,我就调回了中间,正好坐在她的后面。
学习嘛,是再也好不起来了,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了坏孩子,他就很难再好起来。但那时候我很幸福,因为可以天天趴桌上看她的背,一头留到脖颈的黑头髪。她的头髪很漂亮,我从未见过这样天生丽质的,乌黑发亮,像绸缎一样披下来的头髪。虽然不是长髪,但真的很飘逸。
因为我闷闷的,她也很少跟我说话。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有九成都暗恋她,我属于根本没有希望的类型。没有希望,这不表明本人不够帅,事实上,据后来回想,当时班上最俊的难道不是我吗?虽然上大学之后遭到室友的质问:「一天不自恋能死啊?」,但是,至少那时候,本人真的是最帅的——然而也是最不成熟的,要不是天真到那种地步,就不会被狗日的老师糊弄着玩了。唉。
没有女生会喜欢不成熟的男人,豆蔻年华的女孩子更是如此。所以我混得很惨,直到三四年后才熬出头来。
她的脸庞是典型的纯美风格,要不我当初怎会看呆了呢。身材不能说修长,但是极为窈窕。那时候看《神雕侠侣》书,就经常把小龙女想象成她的样子,把杨兄弟想成我的样子,后来老大不小的尹志平跑去干那种龌龊的事情,让我很生气。我想,如果是本人去干这种事情,绝对不会这么龌龊,最后闹得身败名裂,自杀谢罪,临死还不被龙MM谅解。对待纯美的女孩,一定要有纯美的风范,尹志平那种人,简直是和八戒一样的,而且没有猪八戒聪明,所以太恶心了,根本死得不够惨。
那时大家的身体都刚刚发育,每到夏天,全班男生共同的嗜好是偷窥女同学的小馒头,还有漂亮女老师的大馒头。具体方法有请教问题、反光镜、望远镜不一而足。最便宜的莫过于坐在女生正后侧偷看,我就是坐在那个全班男生最艳羡的位子。她有时穿着可爱的小背心,可以轻易看到腻白的胸脯,有次浮光掠影地看到了乳房的全貌,陶醉得没有缓过来,差点被发现。我到现在还隐约记得当时看到的少女乳房的样子。
虽然是少年的暗恋,不算真正的爱,但是深挚到了极处,连做淫梦都是念念不忘的。有一次梦见她在洗浴,朦胧雾色中像是白玉雕的女神一样,依然是纯美的风格,很少色情镜头。水光之中,玉臂润足,曲线玲珑。恍惚中她擦干身子走出去,月辉之下,冷艳不可方物。有意思的是我竟在梦中背起了诗经:「月出皎兮,舒窈窕兮,有美一人,婉清扬兮!」,而诗经中好像并没有完全相同的句子,这是我在梦中乱七八糟拼出来的。
梦中的她回到卧室上了床,翻个身就睡着了。我的视角转向她侧躺的裸体,先是由上而下地俯视:她用一条毛巾被横遮过肚脐和腰围,露着大半个屁股,更不用说两条光裸的大腿。下面的手臂无力地搭在床上,手掌向上,另一条遮过乳房,手心对着床单。视角慢慢放低,我也好像成了一个实体,站在她床侧,慢慢跪下,对着她的屁股。
月亮光从窗外透进来,一切情境好像是真的一样。我也身在梦中不知是梦,下身涨着,情欲撩然地看她被月光涂抹上一层清辉的屁股。两个肉感无比的半球以美得不可思议的弧度紧密闭合在一起,似乎诱惑着人去一探里面的究竟。我知道轻轻地掰开它们,就可以看到少女最秘密的孔穴之一,但竟然犹豫了。因为这样看着已经是对心中女神的亵渎,进一步无礼,难道不是玷污了这个纯美女孩的贞洁吗。我在梦中还这样想。
她突然翻了身,手从乳房上挪下来,放到小腹上。她的脸依然在月光不到的暗处,但我知道她的眼睛是紧闭着的,她是熟睡着的。我大胆地凑到她的胸前,看见她的两个小太阳。真的是小太阳,两对肉团,像太阳一样在暗夜里发着光,粉腻香滑,盈盈一握。它们纤巧的形状,和我曾经偷窥到的一模一样,但在这时向我展示了全貌。粉红的樱桃粒那样乖的生在肉嘟嘟的小丘上,真想亲一下。
但我直起身来,惊讶地发现她现在的睡姿很不雅。她翻过身后,正躺在床上,两条腿叉开,毛巾被滑落一边,露出半侧小腹。更让我几乎脸红的是,梦中女孩的私处完全露了出来,黑色的毛丛扎着我的眼。
我那时还年少,对女人的私处没有多少研究,因此梦中的那个部位也是不清不楚的,何况她的腿并没有大分开,只露出阴阜而已。
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的是她那两条很写意地分开的腿。我是很喜欢女孩子的纤秀脚丫的,而她的脚丫就那样支棱在床尾,一只距离床面四十五度,一只三十度左右的样子。粉红色的指甲,不像是染了丹蔻,因为颜色极自然。我走过去,正对着她的脚心,它们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嫩,端正的脚掌和脚跟泛着浅浅的红润,细嫩的脚趾整齐地依附在一起。我用手托起一只脚,极其微妙的重量,而且,我竟然触到了她的肌肤,而且是她的脚!那只脚丫无力地摊在我的手掌上面。
我在梦中起了色胆,抓着她的脚脖,把脚掌贴到我的鼻子上,脚心对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作为对美女放肆的惩罚,我没有闻到什么暧昧的气味就醒了过来,心跳很快。大概是这种心跳把我弄醒的。然而口鼻处仍然像贴着她的暖暖的脚丫儿一般,舒服得很。往下面一摸,湿湿的。
连这个梦也是很久远的事了
,我做过不止一个关於她的梦,而这个居然是最出格的,因为她在梦中始终是裸体,我竟然斗胆摸了她的脚丫,还把它亲在嘴上。
於是老头把衣物一件一件摊开来,挑出内衣内裤,然后把她的上身抬高,我帮忙扶着肩膀。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世界接触到她的肌肤,没想到会是这个场合。不论人生前如何,死了就全部叫做「屍体」,它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人类的一切对它们不再有意义。不论一个平日如何看重自己身体的女人,死后却被可以这样被脱光了看。屍体有点僵,就这样直直地挺着,我摸着她冰凉的肩膀,已经冷透了。随着上身离开屍床,她的头往后仰着,突然嘴巴张开了一些,露出牙齿。和灰白的嘴唇相比,露出来的门齿稍稍泛黄,不过平日一定是樱唇皓齿的。
我告辞出来,虚虚地飘出校门,搭车去×院。她果然是猝死在今晨八点五十三分,才两个多小时。我找了一位医生朋友,由他带我走到太平间。
「我们刚吃完早餐走出来,她突然就倒下去了」,一个圆脸的女生说,「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刚进去没多久,医生出来说说是猝死——」,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摆在面前的是具光裸的屍首。在拉出来时,铁架床顿了一下,屍体的乳房、小腹和大腿上的肉便同时一抖,我下面立马硬了起来。就像十年前呆看她的脸一样,我站在这具横躺着的精致绝伦的人体跟前,片晌间就这样傻站着。
星期日的早晨阳光明媚,我很快凭姓名查到了她的寝室号码,抱着试试运气的态度,敲开了她们寝室的门。
但W 告诉我的另一件事,让我很难接受。他说,前些年大家念大学时候的一次同班聚会,那几个追过她的痞子绕在她周围,她口中一个一个「哥」叫得可亲热了。
「您不要太难过……医生说不明白死因,我们给她家里打了电话,他们正在赶过来……她的遗体停在×院。」
直到月前一次跟老友W 的谈话,上天入地几个小时之后,说起中学的事情,才偶然谈到她。他说:「你不知道?她现在跟你一个城市的!」,我心头起了异样的感觉。从他口中得知,她考到这个城市念研究生,就在×大。
「等等」,我说。老头扶着她的身子,我从衣物中挑出乳罩,「漏了这个。」
「…嗯……她早上出事了。」
乳罩是吊带的,我们只好把已经套了半截的内衣又脱下来。我抬起她的胳膊,把吊带挂到她肩膀上,我留意到她腋窝中有细细的腋毛。最后把罩杯扣在两个肉团上,后面拉上纽扣就弄好了。她的乳房比当年我在梦中所见丰满多了。背部光洁如绸缎,没有出现屍斑。
和她做了两个月的前后排,三年同班同学,六年同校同学。然后人家考上了名牌综合大学,而我则进了一个龌龊的工科大学玩机油。
说到那个没有一点人文气息的地方,连念诗都有机油味。一次选修课居然出现了「论语选读」这种稀罕东西,我们都很希罕地跑去听,结果那个混账一句话念出三个错别字,我恨不得上去掐死他。本人怎么说也是个半瓶子的文学青年,怎么可以忍受这种虐待呢?我承认,这年头热爱文学的的确少了,但不代表哥们都是文盲啊。那个傻×,把《论语》的「论」念成去声,书名都念错,糊弄鬼啊?
南方的冬季湿冷湿冷的,让在北方上了四年学的我一时不太适应。大家都是刚出校门,各奔前程,个别大专毕业的同学已在社会上打拼了两年。小时候一个个单纯的样子,现在都真正心如其面了。变了变了,谁都变了,我难道没变么?
很奇怪,听说是没来得及正式抢救就宣告猝死的她,又没有经过手术,怎么会被脱光了停在这里呢?而且我看她身上,也没有动过手术的缝合痕迹,衣服是什么时候除去的呢?
我本无意於再见她,但自从知道了身在同城,心里总想看一看也是好的。就这样想着,我今天起步走向×大。
「我是她中学同学,请问她在吗?」
「您现在给她穿上吧。」
「都是这样光着的吗?」我问老头。
他拿来她的衣物,都在一个袋子里。
一个样子很悲戚的女生出来,「您找谁?」
「您好,我找苏兰。」
一头曾经那样打动过我的秀发完全地下垂着,我看着她光洁的额头,觉得很凄惨。
那次聚会我也在场,和她不在一个桌,只匆匆瞥了几眼,勾起几分酸酸的滋味。她这些举动我是没看到的。我想象不出一向清纯的她在酒席上叫人「哥」的样子,人真的变了。我听完后变得沉默,聊了几句,就送别W ,回去蒙头睡觉。
老头拿起内衣,举起她的右手套上去,然后由我扶着头,套上她的脖颈。
一切都是阴冷的,他带我走到那个编号十六的大铁柜,用手打开,然后拉出一具人体。
我没来得及辨认是不是多年未见的她,心便猛烈地跳起来。
在老头重新给她套内衣的时候,我拿起粉色的内裤端详了一下,确认了正反面,走过去替她穿上。她脚丫的尺码也比我梦中看到的大了些,但仍然是那样纤细洁白,左脚拇指上套着个纸牌。一摸冰凉,而且没有了肉感。算算不过两个小时,没想到她僵得这么快。把内裤从脚沿着腿套上去,到大腿根处有点
守门老头一副邋遢样子。我谢过那位朋友,走进阴冷的房间。
他对她颇不以为然。我好奇地询问原因,他说,「贱!」。他给我分析了她中学六年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史,得出这个女人用情不专的结论。这消息对我倒无所谓,因为那时的我虽然傻傻的,对这些事情多少知道些,据我所知,一直是那些男人把她当宝贝来抢,而她巧妙周旋其中,偶尔甩掉两个弱者。她是极聪明的女孩,料想没人能占了便宜去。
然后才把目光转向女屍的脸。
在那个环境里,是很能消磨人志气的,她的影子也逐渐模糊了,到最后一两年,我几乎不再想起她。那个不懂事的花痴少年,也早已不见了。
这句话把我木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了。十年来长久爱恋着的她竟……?好像被人突然摘去一颗心,身体空旷得无以复加,若周围没有人,简直要委顿在地上。
那张脸平静无比,一如她突然失去了生命的躯体。纵然苍白得很,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这些年她的模样有变化,但我总能认得。她的眼安详地闭着,长长的睫毛略弯,就像熟睡了的样子。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微微抿着。
他好像怕是家属,说,「会穿的,刚进来,还没来得及穿。」
「她的衣服呢?」
「什么事?」
又有两个女生走出来,她们有人像是刚哭过。
紧,大概女孩的内裤都偏小。
她的双腿不是紧紧并在一起,可以清晰看到黑色毛丛中的那道肉缝——我曾无数个日夜所想往的地方。老头这时把内衣套上了,架起她的双腋,让屍体的臀部离开了钢板床,我把这件略小的内裤拽上她冰凉的臀部,紧紧裹住。内裤盖上她阴阜的时候,我盯着那个地方,心中颇想看看下面的风光。但仍然很快套上了。
袜子是白棉质料,脚掌脚跟两处有泛黄的汗渍。我把她左脚的屍牌摘下,将袜子卷成卷儿,给她慢慢穿上。看老头穿的,就不如我仔细,微微皱着。她的脚已基本没有了肉感,但脚掌脚心滑滑的,像是运动过后自然风干的触感,仍然挑逗人。
整套内衣都是白色,穿上身显得很清纯,很性感。给内衣整理褶皱时我不断碰到她身上的肉,竟然起了性欲,简直有心如火撩的感觉。当时脸色大概不太对,但老头没注意。
我们又一起给她穿上毛衣毛裤。这里冬天温度不低,但怕冷的女生都还是要穿上毛裤的。
穿仔裤的时候,我把她双腿提了起来,让老头慢慢顺下去,因为有毛裤套在里面,穿起来是比较紧的。两手攥着她的脚脖儿,大拇指捏在踝骨上,触处皮肉柔细,心中有旖旎的感觉。待全部穿好,系上皮带,除了脸色嘴唇苍白,她宛若昏倒在校园的女孩。我知道,三个时辰前当她吃完饭突然倒下时,也是这身装束的。向她上衣口袋里摸了摸,还有一张饭卡。
我向老头要她的鞋子,他慢吞吞地拿出来。死人要褪下鞋袜套上屍牌,出院时家属若不记得要回,这点遗物大概就归给死屍穿衣的这类老头子所有了,所以他才会藏起来。这医院的遗体管理实在不正规,从死人的遗物上显然可以揩油,这让我感到很不对劲。而且从刚才起脑子里面不断出现一具具漂亮女屍,心中难以抑制一股暧昧难明的感觉。
她果然是穿白色的女式运动鞋,这固然是跟仔裤配套的,但我实在想不出她穿皮筒高跟鞋的样子,也想不出她夏天穿长统丝袜的样子。印象中,她一直是清纯唯美到极点,又是个爱运动的女孩子。
但鞋子没有穿,就在袋子里装着。
「她现在要出院吗?」老头问我。
我正要回答不是,并说明我的身份。但非常莫名其妙地,停顿了一下,微微点头。
「手续办好了?」老头问。
我心中后悔,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知自己很不舍得离开她,我心中旖旎的波涛还没有平息下去。但是总不能把她的屍首弄出去啊,这是犯罪的啊。更何况,手续怎么办呢。
「等会就好。」
「我认识××殡仪馆的化妆师,他很行!」
我皱着眉头,心跳得厉害,就像那次在梦里嗅到她的脚丫那样厉害。我对老头说:「我是她的未婚夫,她家人离这儿太远不能赶来」,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塞到老头手中,「这是点小意思。您看,我不能证明我们的身份,她离家那么远,一切都该由我来照顾,不能老是停在这儿。」
老头眨着眼睛。被人冒领了屍体,工作就没了,说不定还要担上什么关系,可万万划不来。他做出一副拒绝的样子,但仍然把钱在手里攥着。
我想,如果有张两人合照的照片来骗骗他,也许好办些,可惜没有,连张毕业照都没有。我问他:「您识字吗?」
「我高小毕业!啥事?」
我掏出手机,把女朋友的名字改成「兰兰」,然后指着屍牌上的名字,给他看,「我们恋爱很久了,这些都是我们交往的信息」,我把身份证掏出来,心想豁出去了,「不会有错的,您登记一下吧」,我努力让后来的腔调变得哽噎,并做出悲伤的脸色。其实我从一进来便很肃穆沉重,曾经的挚爱这样死掉了,本来就是伤心的。
老头看着我的红眼圈,又攥了攥手里的钱,好像是约摸没有问题。他把身份证号码记下来,「节哀顺变,小伙子!」
当我把屍体送上××殡仪馆的丧葬车,心想小医院的管理真松懈到无以复加,竟然把屍体的管理权完全授予这个老头子。初时还忐忑不安怕人查问,没想到事情来得分外容易。
车子绕过一个无人角落的时候,我叫停并付了出车费用。在司机不解的目光中,我抱着她下了车。
洁白了,当然不是像石膏一样白,我在停屍房甚至还觉得有些泛黄色。不论怎么护养,人是不会一点牙垢也没有的,即使是她这样丽质的女孩子。我把鼻子凑上去,想闻出她早餐的内容,但除了牙齿本身的微臭,气味抽象得很。
我皱着眉头,手指划着她的贝齿。两排牙齿不是紧紧咬合的,很轻易就可以打开,里面是粉色的口腔,和略显苍白的舌头,好像还是湿润的。一股混合了豆浆和油炸食品的味道飘进我的鼻子,这便是她的早餐了。我捏着她的舌尖把湿润的软软的舌头拉出来,轻轻吮吸着,上面有她死前进食的味道,还有残留的唾液。
这不是我的初吻,但感受比初吻更加剧烈。我的心猛跳着,双手捧着她的脸,简直要把她的舌头咀嚼下去。我自己的舌头在她口腔内转了不知多少圈,反复舔着她的牙齿。她嘴唇的内侧是香滑腻软的,来回擦着我的嘴,像是回吻一样。
⊥这样趴着亲吻一具死屍,像过了初夜一样漫长。我后来站起身,唇舌麻涩,她则在床上微张着嘴,好像还要。我把她的嘴捏合,苦笑着说,宝贝,够了。
她斜斜地躺在我的床上,依然挺直着,像在停屍板上一样。对於像太平间老头儿那样的大多数人,屍体只是一个记号,代表某个人曾经存在,而本身没有意义,当它们完成最后供人瞻仰的义务,就被烧掉,或者埋下。
但对我来讲,活着的她一直很远,我甚至不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而现在,她的身体实实在在地躺在我身边,乖乖地听我话。多少年来梦想着她能成为我的女孩,在这个愿望一天比一天不现实的时候,今天,她的灵魂已经远逝,而肉体完全属于了我。纵然一夕之欢何其短暂,我又有什么遗憾呢?
我脱去了她的上衣,并解开皮带,开始脱她的裤子。那老头记下了我的证件,如果事情有变,连这个小小愿望也不能达成了。我不惜这么大的代价,一定要完成它。
仔裤很紧,索性拽住毛裤的裤脚,将它们一起拉了下来,露出白色内衣包裹的双腿和白袜的双脚。又脱掉毛衣,她一身白色。胸前鼓起的两个小丘显得很丰满。
我捉住她的双臂拉起来,搂在怀里,把脸埋在她胸脯上。处女的幽香阵阵传入鼻孔,她的乳房还很有弹性,让我心里痒痒的。右手捏过去,是极舒服的两个肉团,隔了两层布,还是肉嘟嘟的。她真的不是当年的少女了,这对大馒头,比我曾偷窥到的大了不止三倍吧。我手上加了力,并且亲吻着。隔着内衣挑逗,比较有情趣,她虽然死了,也要享受这一切。我另一只手向她腰肢摸去,到了越来越柔滑的地方,是她的小腹。按一按,软软的就陷了进去。她还是没有长出赘肉,即便这样弯着腰,脂肪也不显得多馀。再绕过大腿,顺着曲线摸上屁股,感觉很春情。由於内裤的紧紧束缚,臀部肌肉显得硬硬的,我把手滑进她的内衣,先是隔着层内裤摸了一把,继而又滑进紧窄的内裤,捏弄着这两团在铁板上贴了近两个小时的美妙的肉。它们还是冰凉的,当时光着身子被放在上面的时候,一定温热得很,但多么温热的肉体,在那种冰凉的屍床上躺着,不出几分钟也要变冰凉的,我疼惜地想。正捏着,中指突然触到了毛茸茸的地方了,我赶紧挪开,那是最后要抚摸的部位。
几次滑过她的股沟,颇想伸进去捅一捅里面的小洞,我和女朋友调情时就经常这么干。但少时的梦境浮现在心头,为避免唐突佳人的缘故,我认为应该郑重一些——脱光了再说。
但是又亲又摸,好不陶醉,欲火撩人,按捺不住。我从这个紧绷绷的内裤中抽出手,一把放倒怀中的香躯。抓着她的两只脚,倒提起来,V 字型压向她的胸口。让裆门大开,紧俏的屁股翘了起来。我趴在上面,对着她阴部的位置,狂野地喘着粗气。虽然是死屍,裆部也不会没有气味,何况她死之未久。一股淡淡但醇厚的毛髪丛的味道,混合着尿骚气钻进我的鼻孔,我的鼻子在上面摩擦着,嘴唇亲吻着。稍稍向下一点,味道变得臭烘烘,我就这样用嘴对着她的肛门,隔着两层布片。
这时我的欲念膨胀到了顶点,一只手扒在她的裤腰上,正要扯下来。按照平时的程序,的确是可以把女人脱光拽掉小内裤了。但今天要控制好时间。我停住动作,搂着她,做深呼吸,调整情绪。
她的两条腿由高举的V 字型放下来,「咚」地两声响,舒展的伸开摊在床上,没有了平时肌肉松紧的束缚,处于完全无力的状态。我喜欢这种待宰羔羊般的娇弱。她的双足摊开的角度,就像多年前梦中的一样。不知多少人试过梦想成真的滋味,对我而言则是第一次啊。
怀着若干激动的心情,我放下她的上身,走向床尾,跪下来,正对着她的脚丫。
我不知道这和死因有没有关系。
我用舌尖舔过她的脚心,若她是有知觉的,一定会笑着缩脚,我想。但现在的她安静地让我挑弄着,毫无反应。
这样子没有意思,我放下她的脚,将屍体在床上翻了个身,让双足足尖朝下垂在床沿上。把手放在她那只穿着白色棉袜的脚丫上,将它托起来顶着我的下巴,另只手则抓着她裸足的脚掌捏着玩。她的棉袜上面有微微的汗臭味,脚掌软软地抵在我的嘴下面。其实,这双脚可以算得上玲珑透剔,如果没有那个多年来忘不掉的梦,我应该会感到更兴奋些。
我玩着她的脚丫,又把内衣的裤脚往上抹了几分,露出她白生生的小腿。她的臀部则在远方竖立着,那是更能激起性欲的地方。我眯起眼睛看着,把她的裸足贴到我脸庞,感到温差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大。不知是我的脸降了温,还是她的体温回升了。不过刚才澎湃的激情的确已经冷淡了些,是时候采取进一步行动了。
我站起身,抓住她的裤腰,一把将内衣扒了下来,露出光裸的腿,和粉色的窄小内裤。她的内裤被屁股轻轻夹住一条缝,是刚才扳她腿的时候动作过大,两片臀肉过度分开,然后又夹住导致的。我把她夹进股沟的内裤揪出来,重新整理好。秀裤夹到屁股缝里是不舒服的,我的女孩。然后轻轻拍她的屁股,上面的肉微颤着。
我把她上身的内衣向上卷起,露出大部分的背部。这是极为光洁的背,像洋瓷一样,没有一点异色。我的手在上面滑行着。然后,我解开她乳罩的纽扣,把她翻过身子,脱掉内衣的上身。
她的乳罩跟内裤不是一套,上面是纯白的学生装,和我上大学时用望远镜观望女生楼时常看到的样式相仿。型号,我不在行,目测大概在B 与C 之间,是国人比较欣赏的大小。我回忆在太平间看到的那对乳房,并没有因为失去了生命而摊在两边,而是挺翘着,样子极为好看。不过当时并未仔细观察,匆匆便套上了乳罩。
她现在平躺着,身上只剩下两块布,遮掩着最重要的两个部位。另外,还有一只脚上套着袜子。白细细的肚皮泛着下午的太阳光,抹上一层极淡的金黄。头部因为翻身歪在一旁。她脸庞的侧面也极美,依然清秀绝伦,薄薄的嘴唇有着性感的弧线,让我想起她坐在我前排时候偶尔扭头的婉媚的笑。
我把她的乳罩掀起来,看了看这对俏生生耸立的椒乳,用手一捏,它们便颤巍巍地抖。然后把吊带脱下来,完全解除了她上身的武装。
当年的小太阳,现在已经发育成丰满的小山,曲线更加柔和,不像少女那样尖翘了,但珠圆玉润,典雅地朝天挺着。乳晕如五铢钱一般大小,浅粉色,乳头也失去了血色,像脱了水的樱桃。我把脸贴上去,在这两个凉凉的小山上摩搓,不一会儿,嘴里含着了一个奶子,吮了两口。舌头把乳头拨弄了几个圈儿,每亲一下就颤颤的。也许是心理作用,我觉得这是她身上肉香最浓的地方,总也闻不够。
亲了一会,我又把她的身子翻过来,屍体这时比上午柔软多了,已经完全没有「人」的感觉,只有肉体的感觉。我记得小时候看动漫,听日本名侦探柯南说过,剧烈运动之后死亡的人体,屍僵形成得快,消失得也快。大概她的屍僵已经消失了。
又看到她光洁的背部,我忍不住再次抚摸不止。也许是不断搬运的缘故,她身上没有形成屍斑,我想再晚去医院一个小时,她的脊背就不会这样好看了。
之所以又将她翻过来,是因为我喜欢从后面脱女人的内裤,再没有比看到圆滚滚的大屁股慢慢露出来更性感的了。她少女时代的臀部本是尖翘型,后来慢慢变宽,现在我眼前的屁股是圆融浑厚的,但不肥大,仍然保持着和身材匹配的尺寸。我以前非常喜欢她的陡俏纤秀的臀形,现在变了点样子,无法温习旧梦了。不过,我自己对女人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人总是这样的吧。
轻轻捏动着两个半球,我双手从下方探进去,缓缓往下拉。她的尾椎处露了出来,然后股沟慢慢出现,然后是臀尖……我很不爽地看到她屁股右侧隐约有一点淡紫色屍斑,像肿了似的颜色,略微影响观瞻。
当我最终把内裤从她的两只脚上摘下来,还饶有兴趣地翻开看了看里面。我上午在太平间捡出这件内裤给她穿上时,心中是极想观察一下的。里头没有卫生巾,所以有些黄色的污渍直接粘在了内裤上,闻闻,除了靠近尿道和肛门的部位是一股骚臭气,其馀地方还留着洗衣粉的清香,说明穿在身上不足两天,也许今天就要脱下来洗掉的。
她又是赤裸着的了。我上午第一眼看到她时,那具平躺着的裸体刺激了我的眼球。而现在她趴在我的卧室,翘着一个屁股给我看。
我凑近这对屁股瓣儿,心想是不是时候掰开来看看那个梦中未敢看的孔穴。犹豫着,两只手在上面捏来捏去,过了会,由捏来捏去变成了抓来抓去,在她的两片屁股被我抓得分开的时候,我瞥见了她的肛门。
。即便是老婆,也未必肯这样拿私处示人罢。如果一个有知觉的女子被我这样弄,真的要羞死了。
而如果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只怕也不敢对死者这样放肆。如果面对的不是数年来梦寐以求的肉体,也不会有这么强的占有欲。甚至,把一具陌生的即使靓丽的女屍摆在身边,我可能会因厌恶感而不动它一根指头。
她不一样。现在为了占有她,我不惜一切。
把两片蚌肉分开,我看见颜色较深的小阴唇,阴蒂在它上面,下面的阴道口微张着,粉嫩粉嫩的。我捅了捅她的尿道口,还有点湿润的感觉,嗅之有腥臊味,还有些咸咸的汗味,由外阴散发过来。她阴毛上面气味已不明显,淡淡的。我这时反而静下心来,停顿了一下,用双手拇指轻轻掰开她的阴道。
我想,我应该是看到她这里的第一个男人,她的身子完全地、而且仅仅归我所有。我用目光搜索着处女膜,根据已往的知识,我晓得处女膜就在阴道开口处极近的地方。
但事实让我十分难过,这个女人,已经失了身。
我放开手,直起身来。一下子觉得很落寞。她其实是我完全不了解的女孩子,吸引我这么多年的,无非是那纯美的容貌和青春少年无知的幻想附会而已。
我忽然揪起她的头髪,粗鲁地扇了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
她清秀的脸上没有掌印,连微微发红都没有。是的,作为一具屍体,和她生前已没有任何关系,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对美丽的肉,一个符号。而她这个人已经消失了,魂飞魄散,还是上了天国,於这具屍身都无所谓了。
一些像我一样暗恋过她的男人也许会难过,另一些追求过她的痞子也会把这件事作为谈资,甚至叹息着来吊唁一下。她的亲人,当然会哭得很伤心。但数月之后,谁还记得她、时时挂念着她呢?陶夫子说,「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侧躺在她旁边,轻轻抚摸她的脸,一根手指恶作剧似的捅进她的鼻孔里。她现在的体姿之不雅,如上所述。我看着她的身体,那样人事不知,毫无廉耻地分开着腿,露着阴户。她的髪丝凌乱,覆盖了明秀的额头,两手撒开,没羞地挺着两只大奶子。上过她的男人想必没见过这幅景象。当然,她的凹凸有致,肥瘦均停,以及白细的皮肉,这是大家能共享的。但是,想到这里,我又生起气来,但是,我能随便扇她耳光,你小子能吗?一只手又舞起来,半路上停住,悄悄落在她脸颊上,摇着她的下巴。她的嘴嘟起来,露着贝齿。
我缓缓摇着她的下巴,她的刘海儿在额头上方晃动着。这时她的上衣中有铃声响了一下,我翻开衣袋,是她的手机。打开来,桌面是可爱的月下调情图。这条短信来自一个叫「王思」的人,从无聊的内容看是她的男朋友,而且不知道她的死讯,看来不是同城。打开她的收件夹检阅信息,越看越窝火,真想摔了它。
把手机关掉扔在一边,我翻身跨在她身子上,亲吻她嘟起来的嘴巴,把它含在嘴里。然后把整个脸颊吻遍。还有鼻子、耳朵……我轻轻亲吻下去,从脖颈,到肩头、乳房、小腹、肚脐、鼠蹊、大腿、膝盖、腿腹、双足。又翻过她的身子,从下到上。在她的屁股上,我亲了十下,又把两团肉使劲掰开,抠住她的肛门,把舌头伸进去,上下舔弄。她的男人没玩过,想玩又不能玩的事情,我全要享受到。我不会再怜香惜玉,因为她不再是我的女孩,而是我的猎物。
不过究竟感到恶心,我只好起来漱了口,心里又觉好笑:自己实在没什么便宜可占,再这样胡闹就是阿Q 了。虽然乐意怎样就怎样,却也不必自欺欺人,像小孩一样跟死人赌气。她有没有老公与我何干,又不是当年情窦初开的少年了,没道理还把她看成女神一样。眼前这一堆肉,任人肆意玩弄,哪里还有点女神的样子。
把她周身舔遍以后,我正过来她的屍身,把双腿打成M 形,准备上马。现在夕阳已挂,日影昏浊,我准备在黑夜降临之前把精液射进她的体内。暖气机高速运行了一下午,室内温暖如春昼。我脱去衣服,抓着她的双足,把肉棍缓缓插入她凉凉的阴道。里面涩涩的,我的老二有点疼。
但在一圈肉壁紧紧包裹下,我雄壮如马,悍野地冲击着她的花心。把手撑在床单上,身体剧烈地抽插着。她的双足左右轻摇,宛如一对玉枝。我的视线由下面高耸的双乳,沿着发散着瓷器光泽的脐腹,滑落到小腹下面黑绒绒的沟丛。她白花花的双腿之间,夹着我冲锋的武器,她的身体随着我的冲锋而作着机械地抖动,脑袋晃动着,头髪散开。我看到她的小嘴性感地微微翘着,你在呻吟吗,女人?我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拉起来。她的脑袋无力地吊在脖颈上,披散着秀发来回甩动。这么多年,她的髪型竟然变化不大,依然洒脱清逸,在大学校园内,可以被归入短发一族了。垂下的头髪瀑布一样的飘洒,我双手揽住,搂在怀里,然后仰身躺倒。她的屍体趴在我身上,屁股随着我的动作而上下颠簸。
她的头部枕在我肩头,我和她亲吻了一会,把她的上身扶起来,拉动双腿呈跪姿,双手夹着她的双腋一高一低地抬放。她的小腹随着动作的一上一下晃动不已,像缎子一样闪着光,中间圆圆的肚脐眨着眼。我的手慢慢挪到她的双乳上,挤弄着。
,把被子一掀,一个光溜溜的身子从里面滚出
同类推荐:
糙汉和娇娘、
快穿之女配势要扑倒男主、
闷骚(1v1 H)_御宅屋、
乱交游乐园、
她见青山(婚后)、
学长的诱惑_高h、
顾家情事(NPH)、
今天你睡了吗[快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