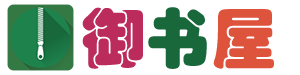这会儿,阮母像个寻常母亲一样嘘寒问暖,阮觅却有些乏了。便没有拿出以前演戏那套,同她演什么关系亲密的母女,而是神色有些困顿地嗯嗯啊啊应几声。
但这副模样落在阮母眼中,却又是另外的意思了。
她有些局促,心想着果然是上回中秋夜里把人的心给伤透了,不然依着这孩子以前对自己敬重孺慕的性子,怎么会对自己这么冷淡?
要说阮母喜欢阮觅多过于阮珍珍,那还真没有。
只是毕竟是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以前又是喜欢黏着她。现在突然许多日不曾过来了,心里自然有些失落。
阮母对于自己之前没有站出来给阮觅说话的事情一直有些愧疚,时间过得越久,这份愧疚便积累得越深。到了现在已经堆满了心间,让她不舒服得很。于是才有了今日的谈话。
她急于去做点什么,用来削减自己的愧疚。
“这天儿渐渐凉了,母亲瞧着你最近穿的那几身衣裳也有些薄了,等会儿便让红菱去拿几匹新到的料子给你做衣裳去。要是不喜欢,可以起去云锦阁挑挑。鳞京那些年纪同你差不多的小姑娘们可喜欢往云锦阁跑了。你若是得空,便出去看看。喜欢什么,尽管挑。”
阮母试探着伸出手,拍了拍阮觅的手。
“要是缺了什么,也可同母亲说,你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没什么是不能说的。”
说话间,还将两张银票塞到了阮觅手里。
一张一百两,两张便是两百两。
瞬间有钱的阮觅:……
万能的钞能力。
她沉默一会儿后,压下浑身困乏打起精神,很敬业地弯着眼睛笑起来,“母亲对我真好。”
仅这一句话,阮母便像是得到了赦免,长长松了口气,心里的愧疚感大消。
“你这孩子,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呢?”她顺势又将自己手上的玉镯褪下来戴在了阮觅手腕上。
眉目慈祥得很,还真像是个全心全意为女儿着想的母亲。
仿佛前几年从不出现,将阮觅视为无物的人不是她一般。
阮觅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脸上的笑完美无瑕。接话也接的很快,阮母那句话刚说完,她便如同一般的同母亲说着悄悄话的小姑娘那样不好意思地垂下脸。
“母亲对我好,我自然是知道的。”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气氛看起来极为和睦。
但从始至终,不管阮觅表现得与阮母有多么亲昵,她与阮母都没有亲密的肢体接触。
就像一个整日演着戏的演员,无声保持着最后的底线。
而阮母今日这样异常的行为究竟是为什么?刚开始时阮觅确实不清楚。但多听了几句话后便能明白过来,这是出于她的愧疚。
阮珵是这样,阮母也是这样,巧合一样通通凑在了今天。
其实阮觅是无所谓的,不会因为这份愧疚是在她来阮家的第四年时,才姗姗来迟而感到生气。也不会因为突然受到关注与怜爱而欣喜。
这些于她而言仅仅是耳边吹拂而过的一缕风罢了。
嗯……但给了银子就不一样了。
她得有敬业精神。
于是这个很敬业的人陪着阮母谈天说地,从阮母追忆自己刚怀孕时的幸苦说到了她小时候带着阮珍珍玩的时候有多累。其间不管说到了什么,阮觅都保持微笑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真有趣。”
天上的日头从略有暗淡到消失,再到换成漆黑的夜空。
阮母尽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又把阮觅留下来吃了顿碗饭。用晚膳的时候阮奉先也在,阮珍珍因为心情不好这几天都自己一个人躲在房间吃,阮珵倒是来了。
这回用的是小圆桌,只坐了四个人。于是阮珵与阮觅便算是相邻。
他看着阮觅气若游丝的模样有些奇怪,吃了几口,终究是没忍住,打破了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绷着脸拿公筷给阮觅夹了点菜,“这个不错。”
阮珵从来没给人夹过菜,动作中透着几分生疏。
阮觅则是一下午都在陪阮母说话,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见阮珵夹了菜,眼睛也没力气抬起来了,只道了声“多谢”。
阮珵再也找不出别的话说,便只能继续用饭。
这场面要是发现在一月前,阮奉先肯定会冷哼一声训斥阮觅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连用膳的礼数都不懂。但是现在他自己都得靠着阮觅去抱顺郡王府的大腿,于是便假装什么也没见到。
最后用完膳,阮奉先放下筷子,丫鬟们过来收拾东西。
阮觅面前的碗碟里,属于阮珵夹过去的那块芙蓉豆腐依旧盘踞在碟子里,完全没有动过。
阮珵看了一眼,脸上终于藏不住失落。
这于他而言,无疑是明晃晃地拒绝了。
要是让阮觅知道他的心理活动,大概只能无语一阵子。她不吃倒真不是因为嫌弃阮珵,只是没胃口罢了。而且那豆腐正巧就是阮觅不怎么喜欢吃的几样东西之一。
不过阮觅并不清楚阮珵这样细腻而丰富的心理活动,就只能让阮珵继续误会了。
————
时间渐渐到了八月末。
院试被称为是科举考试的初阶段考试,考过了便是生员,即人们常说的秀才。
鳞京本地的学子参加院试的地方在东南隅崇文门内。
院试结束后过五天,便可以出成绩。
出成绩那天,阮觅看着酥春抄过来的名单,一眼就看到了殷如意的名字。
第一排第一个,这么明显的位置,要是还看不到真就是眼睛有问题了。
她知道一个院试对于殷如意来说算不了什么,但也没想到殷如意默默用功,然后在院试惊艳了所有人。
包括阮觅自己。
殷如意天赋在那儿,但是中间荒废了这么多年,能再捡起来就不错了,什么案首头名想想就算了。鳞京地界,人多,读书人也多,有钱有势有资源的读书人更多,天才也不罕见。殷如意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能一举成为秀才就已经不错了。
正震惊着,可阮觅转念一想。
男频科举文不就是这样吗?在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打败那些热门人选成为这一届的黑马案首,想想就觉得热血沸腾。
一贯的逆袭打脸套路。
不必惊讶。
于是阮觅又淡定了。
在她想着给殷如意送什么东西当作贺礼的时候,小林巷那位王夫人来到了阮家。
王夫人出身王氏旁支,其实与如今鳞京这支显赫的王氏嫡支已经没什么血缘关系了。从她能嫁给当时已经没落的小林巷的阮家人做填房就能看出来,她自己家中情况也不怎么好。
阮母听到她来了,有些惊讶,但还是让人准备好了茶水点心招待她。
“嫂嫂这儿的茶水,喝起来就是甜。”王夫人不光年纪轻,说话的调子也透着股欢快的意味。
她出嫁的时候不过十七岁,现在还没有过三十,容貌靓丽,笑起来还有股小姑娘家的意思。
阮母盯着她的脸瞧了一会儿,不得不移开视线,省得心理不平衡。
“哪里是我这儿的水甜,我看是你嘴甜罢了。”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但话还是要接的。阮母不善于管家,但现在这样招待王夫人一个人还是做得到周全的。
“我这哪儿是嘴甜?嫂嫂府中用的东西就是好,还不让我说了吗?可我偏要说,嫂嫂这儿啊,不仅水甜,人也好看。不知道嫂嫂平日里是怎么打理自己的?看着我都眼馋,这手啊,嫩得跟十五岁的小姑娘似的。”
阮母喝茶的动作一顿,尽力遮掩住上翘的嘴角,但霎那间待王夫人的态度就不同了。
她清了清嗓子,放下茶盏,“哪儿有什么功夫去打理自己,不过是些从小便用的寻常手脂。拿了白茯苓同芍药晒干,磨成粉末调成脂膏,每日抹在手上罢了。”
“竟是这等精妙的法子,我听也不曾听过。嫂嫂便心疼心疼我,匀我一些罢。”王夫人一个劲捧她,阮母心里高兴,大手一挥便让红菱去拿几盒手脂出来,等会儿王夫人回去的时候方便她带着。
这会儿气氛算是热络起来了。
王夫人心里有着自己的算计,她观察者阮母的脸色,突然十分关切地问道:“嫂嫂可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怎的眉宇之间总有些忧愁?”
就算阮母脸上开开心心的,王夫人也能从别的地方挑起话题。不过她说阮母脸色看起来不好,也是真的。
阮母听到她这样说,不由得一愣。然后又想到了自己最近忧心的事,便叹了口气。
“嫂嫂有什么忧心的事,不妨同我说说。我虽说没什么大的本事,但三个臭皮匠还能赛过诸葛亮呢,说不定也能给嫂嫂出出主意。”王夫人见有戏,眼睛里算计一闪,态度更热络了。
阮母也是实在憋得很了,这事儿她也不知道找谁说,现在王夫人一问,她便忍不住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原来那日阮觅虽然同她有说有笑的,但或许是出于一个母亲的直觉,她能感受到,其实阮觅并没有她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开心。
刚刚退去的愧疚感再次涌上来,压得阮母喘不过气来。
她这人就是这样,心里总是容易想很多,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左右,当她觉得自己有愧于阮觅的时候,又没办法减轻心中的愧疚,便会辗转反侧日夜烦心。
可后面几次她也找不到好的时机去同阮觅谈心,只能自己在心里想着,要怎么做才能弥补这个女儿。
她说给王夫人的话自然是省略了很多,只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弥补阮觅。
王夫人嫁到阮家也许多年了,自然知道阮觅的情况。听到阮母说这件事,她差点没笑出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简直就是送到她跟前的机会。
王夫人放轻呼吸,以免自己的异样引起阮母的怀疑。她做出沉思的样子,然后才道:“我这儿有个主意,不知道嫂嫂愿不愿意听就是了。”
“你且说说。”
“嫂嫂想想,觅儿如今年岁多少了?”
经她提醒,阮母才想起来,阮觅如今都十四,到明年便要行及笄礼了。
鳞京谁家的女儿不是从小就学着琴棋书画,女红刺绣?就算偶尔几个不学,但人家那通身的规矩也是没得挑的。
阮觅自小长在乡野,哪儿懂得什么书啊画啊的,出门不让人笑话就是好的了。这样的孩子,又是身在世族里,要怎么找人家?
阮母突然就焦急起来。
这份焦灼里,或许有几分确实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担心,但剩下的,便是所谓的脸面了。
她认为世族的那些公子哥,大约没谁能瞧得上阮觅的。而能看得上阮觅的,恐怕身份地位都不行,说不定还是个拖家带口的鳏夫。嫁给这样的人,阮母只要想想就浑身难受得很,她的女儿,怎么能下嫁给这样的人?简直是丢了身份。
她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潜意识里便看低阮觅的行为,同时心里隐隐有些雀跃起来。
婚嫁对于女子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要是她帮阮觅解决了这件事,那她这个女儿肯定会感谢自己的。这么一想,心里的愧疚感便一点一点地淡去。
阮母处于这种诡异的焦灼与放松的状态,脸色一时之间有些诡异,看得王夫人眼皮子一跳。
试探问道:“嫂嫂可是心里已经有了成算?”
要是心里真的有了人选,那她今日这一遭算是白来了。王夫人敛下眸子,遮住眸中一点阴郁。
我攻略了四个科举文男主 第82节
同类推荐:
偷奸御妹(高h)、
为所欲为(H)、
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
肉文女主养成日志[快穿系统NPH]、
娇宠无边(高h父女)、
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
彩虹的尽头(西幻 1V1)、
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