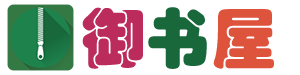闲,意味着没用,意味着罪。
一旦让陆沉某一日停下来,真正闲在家中,或许他才会更为惶恐不安、难以适应。
所以陆沉没有自怨自艾、埋怨命运的时间。仇恨与不公难以挫伤他,他得用呼吸的每一刻钟、每一瞬息,做有用的事,做效率最高的事,为自己赢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陆沉知道自己只是只普通的雌虫,是帝国最不缺的那种雌虫。每年每月每日,每分每秒,都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的雌虫降生于帝国的大小医院。
这些雌虫数量庞大,乌泱泱一群,拥挤在社会的底层下,为生计庸庸碌碌、勤勤恳恳一辈子,甚至连他雌父曾跳进去的火坑——嫁给一只雄虫都做不到。可谁又能说,他们不重要?
谁又能说现在十岁的陆沉,将来不重要?
陆沉从没觉得自己低虫一等,哪怕他的亲生雄父如此嫌恶他们——不,甚至连嫌恶也谈不上,那只雄虫高高在上看向他和他雌父时,眼神是如此轻飘飘的不在意,仿佛在视路边一只微小草芥或蝼蚁,漠不关心,比起嫌恶更让他窒息。
陆沉被迫回头审视自己的存在。
一只帝国绝对不缺的雌虫,脑袋稍稍有些聪明,却也没聪明到惊为天才、一举改变命运的地步。
并不如一般雌虫十分健壮,甚至饿久了还瘦得像竹竿。也并不如一般亚雌纤细柔美,两头讨不了好。
所以他可能是提前把这辈子的运气都花光了,如此平平无奇的他,在如此平平无奇的天气,如此平平无奇的地点,万分之一可能性都抵不上的好运。
——被一个比他小的、十分好看的、仿佛不是一个世界的、温暖的像阳光一样的小男孩遇见了,并要把所有饼干都送给他。
“所以我把这一篮子饼干都卖给你,好不好,大哥哥?”男孩白色羽毛一样的眼睫扑闪着,像剔透的翅膀。
“然后你把这张卡纸都画满小红花,送给我好吗?”
那张方格纸上,被一朵一朵的小红花占满。一笔一划认真勾勒,红得朝气,鲜亮,向上。
“画的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大哥哥你的惠顾!”
“唔,不过还是,每个小红花都稍稍画得不一样吧。”男孩苍灰的瞳仁里闪出一丝狡黠,食指抵在唇上,“嘘,哥哥你得帮我保密哦,被老师发现就不好了。”
……
“啊!顾雄子!老师让大家一起来门口合影了,你饼干卖完了吗?都卖了一下午了!”
有一只和小男孩同样校服的雌虫站在门口呼唤。
“来了——来了——”顾遇的音调拖得老长,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他正把篮子塞到陆沉手里,老师又过来唤:“顾遇同学,来来来,快来拍照了!嗯?那边那个孩子是谁?——那位小同学,能请你过来帮我们拍张照好吗?”
“一张就好,麻烦了!”
陆沉一手挎着装满曲奇饼的篮子,另一手稀里糊涂被小雄虫拉了过去,老师热情地把小虫眼相机塞到他手里。
“嗯,拜托了,这位小同学,一定要把我们全班都拍下来哦!”
陆沉一时被推到全班二年级小学生面前,手里捏着虫眼相机,有些局促。
不甘不愿被拉过去站好的白发小男孩,却抬头,遥遥地冲他这边笑了笑,像在安抚,又眨眨眼,像在说要保密呀。
兴许是那日黄昏的光线太好。
陆沉恍然觉得,这画面确实值得被永远保存下来。
老师还在声嘶力竭安抚:“大家站好一点,站好一点!不要推推嚷嚷,不要大声喧哗!安静,安静!”
“学一下第一排的顾遇同学好吗?他虽然平时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但每次都是最安静的那一个!”
“可老师,”有小朋友举手,“明明是顾雄子懒得说话,也懒得动嘛!”
全班哈哈大笑,老师扶额,顾遇还对着镜头外眼睛含着笑,与周遭仿佛不是一个世界。
这画面,经由另一个十岁男孩的手,被永远地保存了下来。
“我知道了,最后一场笑声!”
顾遇望着游乐场发了一会儿呆,忽然惊醒般道。
“什么?”莫尔一时没反应过来。
顾遇低头兀自说:“我早该知道的,那时这儿除了我们就没什么虫来玩了,之后几天不到,游乐场就被拆除。”
莫尔从他碎碎念的话里觉出了重点:“你以前来过这儿,顾少校?”
顾遇来不及解释,趁着身后那群撵不走的追兵未到,带着莫尔跑到了游乐场前一棵大树下挖了起来。莫尔一头雾水,稀里糊涂跟着雄虫挖着,竟真的挖出了一个铁箱子。
箱子不大,打开装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机甲手办,有熊仔玩偶,有装进信封的信,有各色小纸条,最后底下压了一张照片。
莫尔凑过来看,一时看愣了:“这是……小学的春游合照吗?”
顾遇简短解释:“我小学时曾来过这春游,后来临走时,当时班上的老师让我们把各自的宝贝装进这个时光胶囊里,写下想对未来的自己说的话,然后埋在树下,等长大可以来取走。”
那张合照里,几乎所有虫都是笑着的,就连边上扶额的老师,嘴角也带着无可奈何的笑。
莫尔恍然大悟:“这难道就是‘最后一场笑声’?”
第123页
同类推荐:
末日女骑士[西幻]、
误养人外邪神以后、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
快穿之娇花难养、
她独吞絮果(无限,NP)、
离谱!大神总想艹哭她(NPH)、
末世之世界升级计划、
仙君有病缺个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