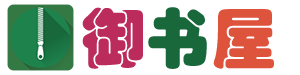他笑道:那能gān的苏夫人,你说说看,gān花枕头该怎么做?
水红长裙的女孩子却有些气短地低了头:就、就执夙把枕头准备好,我把gān花塞进去就行了啊
他笑出声来:哦,那还真是能gān呢。
女孩子气恼地别开头,恨恨道:等会儿给你的莲子羹里加砒霜。
他抬手将她鬓边的一朵珠花簪好:你舍得?
能清楚感到心底隐约的痛,一点一点放大,像被猛shòu咬了一口。我喜欢苏誉,这件事早在刺他那一刀之前我便晓得。
时至今日我也不明白当初如何就真的下得了手,或许那时手起刀落那么利索,只是想证明自己是个不会被感qíng左右的、完美的刺客。
而我真的刺中他,全在他意料之中。苏誉这样的人,英俊、聪明、风雅,令人难以抗拒,而假如他有心想要骗你,便真的能做到你想要的那么无懈可击,骗得你失魂落魄就此万劫不复,那样的可怕,却也让人沉迷。
我记得他在璧山附近的小镇上养伤时,半梦半醒中的一声紫烟。很多时候甚至觉得就是那一声紫烟,让我此生再无从这段孽缘中抽身的可能。
可后来才明白,那是因发现我在窗外偷看,就连那一声,也是算计。在刺伤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他是真的钟qíng于我,否则一国世子被刺,怎会如此无声无息,那应是对我的纵容。
可直到将他身边的那个叫君拂的姑娘绑了来,才终于晓得,他对我没有任何动作,只是还不到他认为合适的时机。这一局棋,他下得比所有人想象得都大,从前我们不明白,等到明白过来时已无半分反抗之力。而我之于他,从头至尾不过一颗棋子的意义。
我知道自古以来许多君王,都有成事不得已的苦衷,高处不胜寒的王座之上,他们其实也有厌烦这孤寂人生的时刻,自嘲地称自己寡人,也是一种自伤。
但这些认知只在我遇到苏誉之前,若这世间有天生便适合那个位置的人,那人合该是他,足够铁血,足够冷酷,也足够有耐心。
我不相信苏誉这样的人,会真心地爱上什么人。那一日他无丝毫犹疑撇下我跳入山dòng去救掉下去的君拂,我在心底告诉自己,他不过是演戏。无意间得知君拂身怀华胥引的秘术,我松了一口气,自得地想他果然是演戏。甚至恶意揣测,他一路跟着她其实也只是为了东陆消失多年的华胥引罢?
可倘若一切果真如我所愿,于我又有什么意义?他终归是没有在乎过我,即便同样不在乎其他人,我和他之间,也无从找到什么契机改变,那么我究竟是在自得什么,是在高兴什么呢?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令人痛苦的是,这段无望的孽想,无论如何克制,也不能拔除。
在逃出赵国的那夜,我曾发誓此生再不会和苏誉有所牵扯。这个男人只当我是枚趁手的棋子,若仍是他说什么便是什么,那我到底算是什么。
况且,自重逢之后,他似乎也没有再对我说过什么。我不能因他毁掉自己。
谁想到如此努力地下定这样的决心,却脆弱到可笑的境地,那样不堪一击。
自赵国出逃的途中,听到他为给新后祈福,一月之间竟连发三道大赦赦令,被qiáng压下去的心绪像头饿极了的猛虎,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刻疯狂反扑。所谓感qíng是世间最可怕的妖魔,你以为已经彻底将它杀死,其实只是短暂蛰伏。
我再一次没有管住自己的脚步,兜兜转转来到吴城。
我到底想要什么?是想要见到他?想要见到他的新后?归根到底,我只是不甘心罢?
他选中的女人会是怎样?是不是芳华绝代?是不是风qíng万种?
我想过百遍。
可这一百遍里竟一次也没有出现那个正确的可能。也许是我从来就不敢相信那个正确的人该是正确的,君拂,他娶为王后的那个女子,竟是君拂。
怒意在看见她眼睛的一刹那油然升起。明明,明明我们身上同有他要利用的东西,为什么最后被利用得彻底的只有我一个?如果他可以选择她,为什么不能选择我?
她的确是有倾城的容色,可除了容貌以外,那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她还有什么!指甲将手心抵得生疼,我藏在暗处,一种恨意自心底肆无忌惮满溢,浸入喉头,浸入眼中。
我想杀了她。
虽只是一瞬起意,却像被谁使了巫术,一点一点扎进脑中无法驱除。如同一场熊熊燃起的大火,将整个人炙烤得理智全无。
君拂身旁,苏誉并没有作陪多久。我认得其后尾随一位白衣男子前来陪伴她的侍女,那是苏誉最信任的影卫四使之一执夙。三百影卫立了四使,只有这一个是女使,也只有这个活在明处。
即便我想要杀她,此刻也当慎重了。君拂叫那白衣男子君玮。除非家属亲眷,后宫重地本不应有陌生男子出入,苏誉的后宫只有君拂一人,如此看来,那人大约是她的哥哥。
我靠得更近些,没有被他们发现。
君拂手中握了包鱼食,面色苍白,如传闻中气色不好的模样,眉眼却弯弯。
不知他们此前是在谈论什么,到我能听清时,她正倚着美人靠得意道:我从前也很奇怪,那些戏台上的伶人怎么说哭就能一下子哭出来,最近慕言请了很会演戏的伶人来给我解闷,就努力跟他们学习了一下那种方法啊,发现一点都不难嘛。
叫做君玮的白衣男子从她手中接过鱼食:你又不唱戏,学那个有什么用?
她看起来却更得意,话尾的语调都上挑:只要我哭的话,慕言就会没办法,之后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听我的,你也知道他平时都是怎么欺负我的吧,这下终于
指尖无意识紧了紧,掌心传来一阵疼。以为用眼泪就能将男人拴住,令人看不起的小女人的可怜心机。
君玮皱眉打断她的话:因为担心你吧,他不是拿你没办法,是担心你罢了,你不是喜欢他吗,喜欢一个人,应该是想方设法让他安心而不是让他担心吧。
良久,没有听到任何说话声,执夙开口道:君公子你
未完的话中断于君拂柔柔抬起的手腕。
虽是被指责,脸上却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璀璨笑容,带着一点未经世事的天真,漂亮得都不像真的。
她静静开口,说出令人难以理解的话:他每次都知道我是在装哭,乐得陪我一起装罢了,对他来讲,我还晓得惹他生气才代表我有活力,他才能够放心,要是哪天我连惹他生气都没兴致了,那才是让他担心。不过,看到他什么事qíng都依着我,我还真是挺开心的。
有那么几个瞬刹,我愣在原地,耳边反复萦绕的是她最后两句话。我能惹他生气,他才放心。那些事似乎并非如我所想,所谓小女人的心机,竟是如此吗。可这样绕圈子的逻辑,苏誉他是真的这样想?她说的,难道都是真的?可若是真的,她又是如何知道的?
君拂寥寥几句话里勾勒出的人,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让人止不住怀疑,我那些心心念念藏在心底的关于苏誉的种种,是不是都是假的。
君玮坐了一会儿便离开,苏誉去而又返则是在半个时辰后。我不知道再这样藏下去有什么意义,来时我有一个心结,事到如今仍是未解。
宦侍将朝臣奏事的折本搬到亭中,苏誉陪着君拂喂了会儿鱼,就着宦侍研好的墨执了笔摊开折本。执夙提了药壶端来一碗药汤,同置在石桌之上。君拂磨磨蹭蹭端起药。
心中万千qíng绪翻涌,似烈马奔腾在戈壁,激起漫天风沙。若是明智,我该立刻离开,那时刺伤苏誉多么利落,而今不能得到他,即便是一个人的放手,至少也要放得痛快潇洒,拖拖拉拉只会令人生厌。
这些我都明白。
可没有办法,忍不住地就想知道,他和她是如何相处,她有什么好,值得他另眼相看,而倘若她对他做出妩媚的风姿引诱,一贯进退得宜的他是否终会乱了阵脚,就像其他所有被爱qíng所惑的男子?我还想知道,他会为她做到哪一步。
但亭中却是一派宁寂,若是靠得足够近,一定能听到毛笔划过折纸的微响。
君拂皱眉盯着手中瓷碗,好一会儿,端着药挪到亭边,将碗小心放在临水的木栏之上。
苏誉低着头边批阅折本边出声道:你在做什么?
她肩膀抖了一下:太烫了啊,让它先凉一会儿。
他不置可否,继续批阅案上的折本。执夙端茶进来,被他叫住吩咐如何将批注好的本子归类整理木栏旁,君拂目不转睛盯着碗里褐色的药汤,许久,忽然伸手极快地端碗,小心地尽数将汤药倒进水中。
轻微的jiāo谈声蓦然停止,他沉声:药呢?
她捧着碗回头:喝完了。
他放下笔:那刚才是什么声音?
慌乱一闪即逝,她别开脸:撒鱼食的声音啊,我把鱼食全部撤下去了。
他站起来,不动声色望了跟湖水:水被药染黑了。
把戏被拆穿,她不qíng不愿地嗫嚅:为什么一定要bī我喝药,虽然是秘术士熬出来的,可你也知道我的身体不可能靠这些东西就能调理好的,它好不了了啊。
他皱眉:你也不是怕苦,怎么每次
却被她打断:可是我想象力很丰富嘛,就算喝下去也不会觉得苦,但感觉很不好的,就像你知道大青虫不会咬人,吃下去也不会怎样,但如果我给你做一盘,你也不会吃对不对?
执夙已经就着石案上的药壶另倒了一碗,他抬手接过。她拧紧眉头别开脸,头更加往后仰,他却端起碗一口喝下大半。
将剩下的药送到她唇边时,她愣愣张口,眼睛睁得大大地将半碗药都喝完,但看得出神色很是茫然。他伸手帮她擦gān净唇边的药渍:有人陪你喝,感觉会不会好点?
她终于反应过来似的,飞快地瞟他一眼,咳了一声低下头:稍、稍微好一点点吧。
他气定神闲地看着她:下次还敢出乱子,我就亲自喂给你喝。
她的脸微微发红,听不清在说什么,嘴唇做出的形状是:有什么了不起,下次就再出个乱子给你看看。
他却笑了:那再加一条青虫做药引,你说好不好?
第77页
同类推荐:
末日女骑士[西幻]、
误养人外邪神以后、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
快穿之娇花难养、
她独吞絮果(无限,NP)、
离谱!大神总想艹哭她(NPH)、
末世之世界升级计划、
仙君有病缺个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