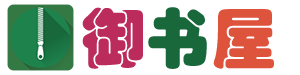爱丝苔尔,那不是在这儿或者那;
是在这儿,而且是现在,萨姆。她16了,半大孩子半大人了,她心目中我像一根傻乎乎的木头手杖。如果有人能同她谈话,如果世上有任何人的话她想听,她相信,那就是她亲爱的父亲。你。但是,她仍然在成长,16岁不是6岁,可你对待她仍像她6岁、7岁、8岁时那样,因为你不想让她走。你妒忌失去她,让她独立,让她学着长大成人,这儿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胡说。
你说胡说?是真理,我说!现在我看得清楚。只要你自己不在危险中,你可以做你的大大的、慷慨的自由主义者。事情都发生在我们家。试婚。《新大众》。埃玛戈德曼、萨可万兹蒂。亨利乔治。维布伦尼。尤金德布斯。约翰里德。林肯肯蒂芬斯。鲍勃拉福莱特。人民党成员。西班牙忠于政府共和者。新政。金西。整个大杂烩。我总是附和你说好。让头脑更宽容,世界更好些吧。总是围着咖啡桌,那就是自由主义者。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如果加以考验,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你把钱都花在我们家里。如果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搬来或打算搬来做你的邻居,你会怎么做?你的心全部投入到你的女儿身上。如果她在阿尔布开克开始同一个墨西哥或印第安男孩关系密切,你又会怎样?你还会说你不在乎黑人吗,尽管你可能因为知道他们在别的地方会更快乐而拒绝他们?你还会说你不在乎墨西哥男孩吗,尽管他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最好还是离开玛丽,因为在现实世界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你还会;
住嘴,爱丝苔尔!萨姆的脸色铁青。你究竟打算把我说成什么?你知道我在大学里为那个要求帮助的前共产主义者而斗争过。你知道我支持过在职工中吸收有色人作教师的请愿。那次请愿在;
请愿,萨姆,请愿是好的,有点勇敢,但还不够。在这个岛子上,你面对的是生活的现实和你自己,并且在第一次考验中,你的表现不像个自由主义者。我不是说我赞成这儿的性教育,或对一个16岁的孩暴露,她还没有作好这么快地接受这种新事,这种基本的事情的准备。当然,这可能对她有点害处,使她迷惑,也可能不会。我们不知道。但你已经在这个周比学校害她害得更厉害,使她更迷惑;由于不支持她,由于在实践中你改变了你在理论上和大话中为她定的标准。她依靠的是她认识的萨姆卡普维茨,而没有觉察到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萨姆卡普维茨。不是玛丽从我们这儿出走最使我不安。是你从我们这儿出走,萨姆。这就是我不得不说的。
他点点头,不再抗议,他的脸灰白,她真想用手捧着他的脸,吻他,求他原谅,但没那样做。
最后,他耸耸肩,朝门口走出。
你去哪儿,萨姆?
去找人,他说。
他走后,她怀疑他是否是去找玛丽;或许是找萨姆卡普维茨,自由主义者。
在下午3点钟以前的20分钟里,雷切尔德京将进行今天的最后一个约见。她坐在用作办公室的空草房里,身旁是当作精神分析病床用的露兜树叶垫子,抄写着关于那个樵夫马拉马和那个不满意的妻子图帕的诊疗笔记。完成这项任务后,她估计第三个患者快到了。
雷切尔把专为访问海妖岛准备的职业活页笔记本放到一边,拿起她杂乱地记录自己生活情景的长方形帐本。莫尔图利因为同她的关系(和她关于他的想法)不是为了发表,已经从笔记本上完全转到帐本上了。
打开日记,雷切尔发现已6天没记了。上次日记简洁、隐秘,除了她自己别人谁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上面写着:
头天节日。日常两次约见后,参加游泳会。兴奋。我队一人,马克海,参加了。表现不错,直到最后表现差劲,但符合他的个性。夜晚去户外跳舞,哈里特和丽莎都参加。后来,晚,同意和一土著朋友结伴,莫尔图利,乘独木舟去附近珊瑚岛。像卡梅尔海岸一样浪漫。我们游泳。我差点淹着。后来在沙滩上休息。值得纪念的夜晚。
她检查着这段文宇。换个别人,比如乔摩根,会读出什么?什么也读不出来,她满意地断定。即使卓别林也无法弄懂。人们的真正历史只是写在脑子里,同他们的遗体一道安全地、无人知晓地进入地下。纸上的任何东西只是事实的1/10。但随后又记起了她读过的书,她的前人的聪明智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根据留在纸上的记录来解释列那多达芬奇的真实生活,他所需要的多么少啊。还有玛丽波那帕特,她要了解波,解剖他腐败的灵魂,所需要的材料是多么少啊。还有,她自己的那段写到纸上的东西温和、随便、毫不显眼,也许只有值得纪念的夜晚这个谜语除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值得纪念?但一个夜晚,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国,值得纪念可能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或一种气氛。世界上谁会知道对作者来说值得纪念的是因为在她一生中这是她第一次极度兴奋?
雷切尔兴致很好,无所顾忌,把笔放到帐本上,开始写:
第180页
同类推荐:
末日女骑士[西幻]、
误养人外邪神以后、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
快穿之娇花难养、
她独吞絮果(无限,NP)、
离谱!大神总想艹哭她(NPH)、
末世之世界升级计划、
仙君有病缺个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