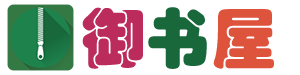他坐到床边,踢掉拖鞋。
一个好夜晚,亲爱的,她说。进行顺利我感到高兴。
是的,他说,但某种不赞成的东西掠过心头。只有一件;
他溜进毯子,但仍用一只胳膊支住身子。
她显出困惑的样子。
只有一件事烦我,克莱尔,他说。你中了什么邪,使你在完全陌生的人面前说话如此随便?说了那么些赞赏性节日、希望我们这儿也有那种放纵的话。人们会怎么想?这给他们坏印象,他们不了解你,他们不知道你在开玩笑。
他伸手关了灯。
我是开玩笑,马克,她在突降的黑暗中说。对于原始民族的自娱方式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收兵,因为我见到你生气了。
刚才,他的嗓音,尽管对她有所批评,仍然饱含对她的企望。现在,突然变了,企望变成了不高兴。什么意思;我生气了?这是什么意思?
噢,没什么,马克,请;
不,我在问你;那是什么意思?
那意味着,每当我偶而谈到性;相当窄见;你就恼火。结果总是这样;因为某种原因。
因为某种原因,嗯?
马克,请别夸大其词,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累坏了;
见你的鬼不知道说什么。我想知道你脑袋里真正在想什么,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早晚你最好成熟起来,变成一个懂事的已婚女人,不是;
她感到软弱无助。不是什么,马克?
瞧,我们不谈这个了,我也累坏了。
他坐起来,离开床沿,床晃了一下。他找到拖鞋,重新穿起,在黑暗中站起身。
马克,怎么了;你到哪儿去?
我到楼下去喝点什么,他粗暴地说。我睡不着。
他蹒跚着穿过房间,碰到一把椅子上,然后出了门,下楼去了。
克莱尔仰卧着,穿着那套多余的白色睡袍,一动不动。她有点后悔,但这也不是头一次。奇怪的是,这种偶然发作都是一种模式,她能看得出来。每当她复述偶然听到的与性有关的一个故事,一个笑话或一段闲话,每当她坦言所闻,他总会对她产生恼火。上次是两周前,也是在这么一个温馨时刻。他们到影剧院看了场电影,主人公是位获奖拳击手。后来,当她评论男演员的强壮外貌和体魄并想分析他对女人的吸引力时,马克却早已选择好他的评语作为不能苟同她的理由。是的,不知怎的每次克莱尔以赞成的口吻提到性或性学领域的有关问题,马克就将此看作一种人身攻击,一种对他的男子尊严的瓦解。在这种时刻,几乎是一转眼,他的和善、他的幽默、他的成人气就会消失,剩下的只有紧张和自卫的气息。老天有眼,这并不经常发生,可还是发生。随后她就同以往那样,陷于茫然。他多怪呀,她想,于是就担心,在那种时刻有什么会烦扰他呢?随之又想这种无端发火是否所有男人都这样?
睡意浓浓,她回想了情窦初开之时和婚后生活,她11、2岁在芝加哥,15、6岁在伯克利,18、9岁在韦斯特伍德,22岁时遇到马克。通过某些途径,她能把过去的梦同现实联系起来。在婚姻里有某种舒适和安逸,尤其是白天。在夜晚,唉,像今晚,在梦和现实中间的裂隙深不见底。
他在楼下喝白兰地,她知道。他将呆在那儿等她睡着了才上床。
她力图入睡,但1个小时过去也没睡着。
他终于回到卧室,她假装睡着,她希望他愉快
12
像波里尼西亚传说中的那只褐色巨鸟,两栖飞机飞翔在高高的夜空,准备降生一个伟大的开端。
大洋洲有着许多造物之谜,但克莱尔海登今晚所相信的一个是:在无垠宇宙中存在的只有温暖的原始海洋,在它上方飞着一只巨鸟,鸟往海中下了个大蛋,蛋壳破了出来了神,塔拉,他在海之上造了天和地,并且造了第一个生命。
对于处于半睡半醒中的克莱尔,很容易将奥利拉斯马森船长的水上飞机联想成波利尼西亚传说中的巨鸟,一会将在南海产下三海妖伊甸园,那里将是他们的唯一世界。
他们在晚上离开帕皮提,现在仍然是黑夜,克莱尔清楚,但时睡时醒,已经不清楚他们现在到哪儿了或者已经飞出多远了。她知道,这个谜是拉斯马森从一开始就有意制造的。
克莱尔坐在破旧的座椅上,这10个座椅是副驾驶员理查德哈培重新装上的;主舱在他们到来前曾被用来装货;座椅不舒服,克莱尔坐直身子,伸开腿,试图让眼睛适应这种暗淡的电池灯。为不打扰坐在她右边位子上打盹的莫德,或她左边过道对面正在打着轻微呼噜的马克,她摸着座位底下和又摸着过道旁,摸她那个带背带的装着一切用品的旅行包,找到后,掏出了烟和打火机。
一吸烟就完全醒了,克莱尔环顾四周,仔细看了看这个拥挤的主舱内部。除了他们3口,除去拉斯马森和哈培在驾驶舱内,还有7个队员。在微弱的灯光下,她数着人头,下意识地寻找着另一个同她自己一样醒着并且内心充满期盼的人。
第55页
同类推荐:
末日女骑士[西幻]、
误养人外邪神以后、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
快穿之娇花难养、
她独吞絮果(无限,NP)、
离谱!大神总想艹哭她(NPH)、
末世之世界升级计划、
仙君有病缺个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