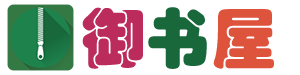谢无咎留下奈何府的烂摊子,陆行焉和谢欺山都束手无策。
不久前,陆行焉就打探到了他在李洪崖的府上。
这个时候,她若去找他,只怕会换来一通羞辱。
陆行焉接手了奈何府事物,才知道谢无咎除了性情太过乖戾,处事能力都是一流的。江湖上各门派这么多人名,他都能记在心里。
谢欺山道:“无咎从小就很聪慧,又什么都想胜过我,所以格外好学。”
陆行焉问:“他小时候,也很可恶吧?”
何止可恶,那时的谢无咎,就是谢欺山的噩梦。
“其实现在想来,他也许只是想让我陪他。”他想起谢无咎年幼时嚣张的样子,笑了出来。
谢侯被杀,江湖无主,剩余的八大门派乱作热锅上的蚂蚁。
有人想趁机冲洗江湖格局,既然谢侯府已不能管束江湖,他们就令立盟主。
八大门派再次集结起来,给奈何府送来一张英雄帖。
十天后在长辛山推举武林盟主。
谢无咎不在,也不能让半点武功都不会的谢欺山出席。
陆行焉最后决定,由她替奈何府出席。
谢欺山担心她武功尚未恢复,若要动武,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陆行焉道:“不必担心,他们既然要用推举的法子,定是在武功上没有信心。如今他们群龙无首,说不定不等咱们出手,就自相残杀了起来。”
谢欺山愧疚道:“这本是谢家的事,不该将你牵扯进来。”
陆行焉叹口气,她这辈子,注定是要给谢无咎收拾烂摊子的命。
夜里她和谢欺山分开后,途径后山。
老树纷繁枯枝上,挂着一张孤零零的生死符。
那时四年前她参加疾青盟会前,谢无咎为她挂上去的。
十天后,她会亲自取下那张生死符的。
她不后悔四年前离开奈何府,也不后悔再一次回到奈何府。
一张生死符,唤回了很多记忆。
她一直以为自己知道宗主是个什么样的人,原来,从没看透那张面具下的苦涩和无奈。
她敲敲自己的脑袋,骂道:陆九,同样的错千万别犯第二次。
陆行焉出发去长辛山前一天,将明镜刀擦拭了一番,她原本想要带着明镜刀,可是又不愿明镜刀沾染别人的气息。
她去藏刀阁找了一圈,也没挑到一把满意的刀。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人是如此,刀亦是如此。
最终,她还是带上了明镜刀。
因去的事长辛山,是沈行止的家,她与沈行止同行。
她们都很久没见过赵行风了。
提到赵行风,沈行止就来气。
“一个只剩一条手的人,还敢四处乱跑,不怕被人当乞丐欺负吗!”
陆行焉掩面偷笑,江湖上多的是缺胳膊断腿的人,大家可都活得好好的。
不过,像沈行止和赵行风这些人,他们出身于江湖有名的门派,又在奈何府这样的组织里长大,从来不知江湖另一面是什么样的。
江湖不止门派间的勾心斗角。
在他们看不见的那个江湖里,有人缺胳膊断腿,有人穷凶恶极,可所有人都活得自由自在,不必承受他人的目光。
善也源于自我,恶也源于自我。
“断臂未必是坏事尤其师兄断的是常用的右臂。当他用不熟悉的左手握剑时,是一个重新修行的过程,有过去经验的铺垫,只要他下定决心,一定会大有所获当然,我只是说习武方面。”
“阿九,我内疚。若不是救我,他不会失去手臂的。”
陆行焉脑袋倚在马车车窗前,若有所思。
“师兄为了你,性命、尊严都可以不要,何况只是一只手臂呢”
赵行风断臂,陆行焉是直接因素。
可她并不后悔。
当初赵行风帮谢无咎骗她时,注定要付出代价。
只不过,这个代价是她亲自施加的。
沈行止并没有为赵行风断臂一事和陆行焉生嫌隙。
她和赵行风,固然是恋人的关系,但这世上不是只有这一种关系的。
一个人,除了男女之爱,还背负着许多其它的责任。情爱固然美妙,却不能为了情爱,抛弃是非观。
她也不会因赵行风失去手臂,就不爱他了。
陆行焉心生一念。
“师姐,也许师兄此次也会来长辛山。”
“是吗”
沈行止心中亦有此念。
长辛山,是她的故乡。
赵行风,也许会来见她。
二人行到长辛山下长辛门的通关处,之间,一人青衫,独臂持剑。
沈行止的脸上立马挂满两行泪,向他奔赴过去。
“赵行风,你这些天去哪了!”
她双臂紧环住赵行风的腰,风拂来,他右手的袖子空荡荡。
她的泪不禁更多。
赵行风左臂抚上她的背:“我无事的,而且,如今已经习惯用左手使剑了。”
陆行焉从马车上走下来,见只有赵行风一人,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赵行风对她道:“当日我发誓以后会听命于师妹,这些日子勤加练剑悟道,如今终于悟出何谓无我之境。此行有我护着师妹,师妹有何所想,尽管放心去做。”
陆行焉拍拍他左肩:“有劳师兄了。”
三人上山,路上,赵行风将自己打探的情况告诉陆行焉。
四年前,九大门派失去一把手,四年后,剩下的八大门派又失去第二把手,此时采取推举的方法选举盟主,纯属没有能以武功镇压全场的人,完全是出于无奈。
陆行焉从来瞧不起这些虚伪的名门正派。
他们英雄帖上写的是不愿大动干戈,所以采取以德选贤的方法。
但是当年结盟攻击苍青派,可是动了很大的干戈。
想壮大门派名声,仅靠合纵连横之术,而不是潜心修习,提升自己宗派的武学。
既然是追名逐利,便不要侮辱武学二字。
江湖许多大善大恶中,有一种恶,是恶而不自知,叫做虚伪。
赵行风此次不止打探了各门派之间的情况,每个门派内部的各色交易亦打探清楚了。
不出所料,在明天的盟会之前,也就是今夜,会有一场没有动静的厮杀。
各派代表都十分谨慎,甚至连他人递过来的酒水都不愿碰。
陆行焉接过仆侍递来的茶水,并无顾忌地饮下,她饮茶的瞬间,所有人都盯着她看。
她就不怕茶水里有毒吗?
不怕。
她是纯阴之体,单纯的毒药对她无效。
见一个年轻女辈如此坦荡,剩余的这些门派代表被激起自尊心,有沉不住气的人已经拿起茶杯,一饮而尽。
最后所有人都喝了茶。
陆行焉他们居住的阁楼外,一夜厮杀。
赵行风担心他们的安危,欲出去探风,陆行焉摇头道:“倒不如好好休息一夜。杀人能弄出这么难听的动静,怎么还好意思动手。”
她从小就被教诲不可为了杀人而杀人,那是刽子手,而不是杀手。
奈何府的一切,都要整洁干净,即便是杀人的刀口。
第二天,参加盟会的人数比昨天少了三分之一。
陆行焉被安排在角落里,她静静看着各门派之间舌战。
其实,若他们真的愿意通过选贤的方式选出盟主,也不必特意聚在此处了。纵观剩下这些门派,大家当年都是一起作恶,又一起洗白的,所谓的德行,半斤八两。
陆行焉有些困,最后听他们定论说要用比武的方式,她的困意瞬间消散。
不过,他们说要比武,大抵是没把她算进去的。
各派选出武功最高强之人,进行车轮战,谁能守住擂,大家就听令于谁。
所有人面面相觑,都不愿做守擂之人。
陆行焉素来不爱在人前出风头,但是那个位置,让她蠢蠢欲动。
她习武十四年,见过江湖游侠,也见过地穴活尸,虽习气宗,却擅于刀法,她守过魍山陵的孤独,也受关山高人前辈们的教诲,她发自内心地想要站在万众瞩目的位置。
只有站在万山之巅,才能一览群山。
可是,屠户的女儿也能站上巅峰之位吗?
她握着明镜刀的手,经脉忽然颤动。
曾有人为屠户的女儿攀爬雪山,取这一把绝世宝刀。
还有什么高峰是不可攀登,有什么鸿沟不可跨越。
她起身,淡然走上擂台。
江湖各派见是她,现是面面相觑,而后有人道:“我们可没说允许女人参加的。”
陆行焉道:“你们也没说不许女人参加。还是怕自己打不过一个女人?”
“这”
四下确实慌乱了。
“现在谁都知道你们奈何府和谢侯府的勾当了,怎还有脸角逐盟主之位?”
陆行焉讽笑:“既然如此,何必邀奈何府前来?”
陆行焉·杀欲
陆行焉将明镜刀从刀鞘拔出,将刀鞘扬手扔向赵行风。
她今日依然是一身朴素的淡青色衣衫,而手中宝刀熠熠生辉,与她相比,太过招摇。
“江湖本来就是以武服众之地,诸位若因陆行焉是妇人,而不愿陆行焉争取心中所想,与朝廷里的酒囊饭袋有何不同?若是诸位仍不愿,可每年相约此地,谁能打得过陆行焉,陆行焉愿让出盟主之位。”
众门派的人也明白,无论他们多少次勾心斗角,真正有话语权的,仍是武功最厉害的人。
江湖之所以叫江湖,为人所向往,是因它最开始的时候只靠武功高低而评是非,而不是自私的人心。
陆行焉所提出的,确实是个折中之法。
今年他们打不过陆行焉,只要回去勤加练功,明年也许就打得过了。
某一门派人的暂任掌门人道:“我先来。”
他也是刀宗,由他第一个和陆行焉对战,再合适不过。
陆行焉微微颔首。
比武的过程,不必有废话。
其它各门派也各怀心思,让陆行焉守擂,其实不是件坏事。这意味着,她得从头打到尾。
天下任何要借助兵卸的招数,都有破绽。
陆行焉若执意用刀,等到了最后,他们一定能找出她刀法的破绽。
半天下来,陆行焉斩断两把刀,断了一个人的发。
她赢得十分轻松。
第四个要和她对阵的,仍是修习刀宗之人。
此人习刀三十年,信心满满他已经记住了陆行焉方才所用的刀法。
然而实战之中,陆行焉的刀法变幻无穷,她所用的招式和前三局的似乎是相同的,可使出来却像是一套崭新的刀法。
明镜刀与她相辅相成,在她手中,刀不仅是一个工具,而像是她的同伴。
最后,陆行焉以收走对方武器胜出。
对手诧异地看向她:“姑娘如此年轻,如何练得这一身刀法?”
陆行焉朝他拱手道:“是先生承让。先生的刀法,应不在陆行焉之下,请问先生练刀有多久了?”
“整整三千天。”
“我练刀已有三千四百二十一天。”
这只是她只练刀法的日子,不包括练内功的时间。
对方接过她扔来的刀,爽朗大笑几声:“陆姑娘虽年轻,但持刀资历更胜于我,陈某输得心服口服。此次回去,定会勤加练功,争取明年能与姑娘一战。”
当年被她杀死的九大掌门,正是各大门派武学巅峰。
她可以从九大掌门联手的情况下全身而退,更何况剩余这些小喽啰。
剩余几人不愿再给她送人头,直接认输。
陆行焉尚未打尽兴,她指着其中一任,道:“该你了。”
剩余的人自然也是轻松落败。
这时,练刀三千天的陈某道:“由一个女子,率领我们剩余的这些杂碎喽啰,倒也是别开生面。”
此次英雄盟会,比陆行焉想象中轻松许多。
往后,她就是陆盟主了。
不是奈何府里的工具,也不是谁的女人。
原本的江湖十大门派,如今只剩八个,其余八大门派又无可以领导之人,眼下重整江湖,最重要的是重新订一套制度。
陆行焉心中早有她的想法。
“既然想要恢复江湖盛世,先得恢复十大门派。诸位内部如何委任,奈何府不会再作干涉。至于长辛门,我师姐是长辛门后人,由她任长辛门掌门,倒也合适。拜诸位所赐,仓青山众弟子颠沛流离,如今,便请各位找回仓青山离散在外的弟子,重建仓青山以赎当年罪过吧。”
新入江湖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听起仓青山这个名字了。
仓青山,正在渐渐被人遗忘。
可是死在关山的张风清,她活在陆行焉心里。
结束这场会晤,陆行焉直接回到关山。
她将仓青山近况告诉晓天,晓天沉思片刻,单膝跪下。
“阿九姑娘对仓青山的恩德,晓天不会忘记。”
陆行焉此行正好赶上晓天阿芬女儿的周年宴。
关山邻里齐聚在此,只问今夕。
陆行焉耐心地跟围上来的女子们讲述江湖的样子,那地方不好不坏,吵吵闹闹的,比不得关山。
阿芬的女儿长着一双动人的大眼睛,若张风清见到,一定很喜欢的。
她临走前,来到张风清旧居。
这一年晓天阿芬时常来此打扫,屋内仍是干净地不染一尘。
好像张风清随时都会推门而入。
她从张风清家里攒银子的罐子里,把张风清欠自己的银子都拿了回来,又将当初晓天给她的仓青山令牌放在张风清枕头下。
她离开时,将路上采的野山菊插在她门前。
陆行焉一战成名,消息很快传到边关。
谢无咎耳闻此事,并不吃惊。江湖是比武学造诣的地方,陆行焉有着巅峰的造诣,就该站上巅峰之位。
江湖一定再找不出第二个像她那样专心认真之人。
一个人能为一件事放弃其他所有,必有成就。
他近日心魔愈盛。
每次闭上眼,他杀谢方怀的场景就会重现一次。
他日夜被这个噩梦折磨,甚至不敢闭眼。
李洪崖不懂事,没收走他屋里的镜子,他无意中望过去,只见镜中男人双眼四周一片乌青,下颌布满胡渣,再加上脸上那一道疤,可不是个弑父的恶人吗?
他一拳击碎镜子,镜子的碎片扎进他手里,他不觉疼痛。一股邪火自他丹田涌入血脉之中,碎裂的镜子中倒映出一双血红色的眼。
李洪崖听到动静,跑过来,只见谢无咎的青筋自脖子上起伏至太阳穴,他双目呈腥红的颜色,那道劈开他面部的疤好似要裂开来。
他像个怪物。
李洪崖立马叫来府中侍卫。
他们拿着尖锐的武器,刺向谢无咎。
可是,李洪崖低估了他。
走火入魔的谢无咎,他拥有比活尸更要强大的力量。
他可是在活尸身边长大的纯阴体,区区兵刃,不足伤他。
刀剑划过他的皮肤,刺在身体上,他完全不知疼痛。
谢无咎以肉身突破李洪崖的重围,来到李洪崖身边,右掌成鹫爪之态抓向他的头部。
李洪崖直接被他捏碎头骨而亡。
李府那些侍卫,也算是见过一些事关生死的大场面,但活活捏碎他人头骨的死法,他们从未见过。
家主已死,这些侍卫心道,保命要紧,于是纷纷扔下兵器,四处逃窜,哪还管李府剩余妇孺的性命?
杀戒已开,再也收不住。
何处有人的气息,他就去往何处。
李洪崖的小儿子听到外面声音热闹,跑出来看,只见院中空无一人,只有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持着一把破损的剑。
小男孩愣在原地,不知道要逃命,也不知道要喊人救他,而是在原地恸哭起来。
“你哭什么?”
谢无咎疑惑地问。
这孩子什么都不说,哭得他心烦。
他扔下剑,走向李洪崖的小儿子,一手捏住小孩脆弱的脖子将他举起。
“别哭了。”他不带任何感情地命令道。
谢无咎,别哭了,就算你被活尸吸干血,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你想做个懦弱之辈,默默无闻地死在这里,还是活着出去?
“不许哭!”他突然动怒,手掌不断用力捏向那个孩子。
小男孩肺部的空气被挤出,他的气息变得破碎,已哭不出声。
没有谢无咎的江湖,正在欢歌笑语,生机勃勃地迎接新盟主和全新的江湖。
边塞苦寒,风雪无眠。一个弱小的生命正在谢无咎的手上流失。
他从来不在乎杀死谁,反正这世上也从无人在乎过谢无咎。
小男孩的呼吸越来越稀薄,忽然,一股干净的真气流入谢无咎体内。
他的意识随着这道外来的真气回流。
随着这股真气短暂控制住谢无咎,他手中的小男孩被人迅速夺走,救回一命。
陆行焉·报复
孟至清七天前就到了弼马镇,他得知谢公子在李洪崖府上的事,生怕李洪崖又对谢公子不利,这些天就一直在暗中守着他。
今夜他若晚出手片刻,这个小男孩就要死于谢公子手上了。
孟至清救回小男孩一命,心生出欢喜。
救人一命,就是他的欢喜。
“和尚,你怎在此?”
谢宴重新有了意识,见到是孟至清,并无喜悦感。
孟至清将自己这一年的经历不分具细地陈述出来,说到最后,谢宴已经疲乏地睡去。
经历昨夜一事,二人断然不可留在弼马镇了,谢无咎从李府盗来两匹马,二人连夜骑到近郊的野地里。
孟至清这一年游走北境各国,走遍了,便要回去破云寺了。
孟至清不大会骑马,他慢吞吞地跟在谢无咎身后,到一段岔路口前,谢无咎停下来等他。
孟至清赶到他身边,问:“谢施主,你要去何处?”
江湖之大,山高水远,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我还有件事要办,你可认得去破云山的路?”
孟至清想了想,他并不认得。
他摇摇头,却自信地说:“我可以问路的。”
他拍拍和尚的肩膀:“那我们有缘再会。”
孟至清愣了一下,道:“谢施主若无处可去,可以到破云寺来找我。破云寺只我一个人,也怪害怕的。”
等他说完,谢无咎调转马头,朝奈何府的方向奔赴去。
每到寒冬,谢欺山的身体就变得格外差,他畏寒,身上总要裹上一层厚厚的毯子。
陆行焉昨日刚回到疾青山,这次,她把萧声声也带来了。
谢欺山生气地问:“你带她来做什么!”
“她有了身孕,来到疾青山,好歹有人照顾她。”
谢欺山呆在原地。
陆行焉脱掉身上披风,立屋檐下甩去披风上的风雪。
“谢欺山,你要做父亲了。”她笑盈盈地说,“萧声声怕你不愿见她,都不敢进来。”
她给谢欺山的书房点了支味道清淡的香,检查完炉火,便离开了。
良久后,吱哑一声,门被推开。
萧声声站在门口,不安地向里面张望。
谢欺山愣将身上的毯子扔到一边,不顾门口风雪,疾步上前抱住了她。
“蠢丫头。”
萧声声亦环住他,她开朗地说:“谢欺山,你这么久不来看我,我以为你死了呢。”
陆行焉望着屋内一双人影交叠,欣慰地笑了。
这时,奈何府的人送来消息,说是宗主在奈何府等她。
天色已晚,又是大风雪。
陆行焉道:“我明日再启程。”
她不知道谢宴此时出现,到底出自什么目的他要来杀谢欺山么?还是要来杀谢夫人?
还是和自己有关的?
陆行焉坐在窗前,望着飞扬的大雪,她许久地失神。
当年她离开奈何府,就是这样的天气。
她手中握着明镜刀,刀鞘上嵌着的宝石硌着她手心。
她摊开手掌,只见自己一双手似完好的白玉,没有任何练武留下的痕迹。
她想,是不是自己把他想得太坏了
她倏地起身,披上披风,握起明镜刀,带上风帽走入大雪中。
抵达奈何府,已经三更,她冻得不能言语,十指僵硬,无法伸展开。
未待她暖和起来,一个炽热的怀抱,似一堵火墙将她禁锢。
“谢无咎,你放开我。”
她挣扎了一番,但谢宴极为霸道,他不给她任何空间。
二人纠缠的时候,她的风帽落下来,青丝流泻而下,谢宴捧住她的后脑勺,朝她唇上咬了下去。
陆行焉咬紧牙关,不让他舌头进来,谢宴便咬她的唇,她的唇瓣被咬破,他尝到血的味道,才松了口。
他冲她调皮一笑:“陆行焉,恭喜你终于站上了万山之巅,整个江湖都要听令于你了。”
“你放开我,好好说话行不行?”
“我放开你,你就跑了。”
话罢,见她有片刻的松懈,谢宴的舌头立即窜入她的牙关,挑起她的舌,与她撕缠。
陆行焉身上的寒气被他驱散,她的披风被扯下来扔到地上。
谢宴将她横抱起到榻上。
年少时,他们就是在这张榻上抵死缠绵的。
那份属于陆行焉的从容,在谢宴面前全都不见,她一巴掌拍在他脸上:“你真是个疯子。”
谢宴被她打了,还死皮赖脸地笑。
“你若高兴,多打几巴掌。”
他急切地褪下陆行焉的裤子,卷起她裙摆,将自己的性器释放出来,不加任何抚慰,直接入了进去。
身体被强行侵占,破开的疼痛占据陆行焉的身体。
谢宴连着几十下猛烈地抽送,陆行焉险些疼死过去。
他看着她难受的神色,轻笑了笑,舌头忽然舔入她耳朵中。
这是陆行焉受不了的刺激,随着他暧昧的舔舐,二人交合的地方开始渗出花蜜来。
“我这样对你,你恨不恨?”
他说话的同时,狠狠送入一记,阳物直入到最深处。
他们接触的地方传来清亮的水声,陆行焉双手扣在他肩上,催促道:“你快一些。”
谢宴的五指穿过她的发,凝视着她潮红的色:“你自己要的,不要后悔。”
他用力挺送自己精瘦的腰身,每一次都要入到她最深处。
陆行焉被他冲刺的动作晃得无法稳定,只得紧紧攀住他。
在剧烈的交合中,她第一次这么热切地拥抱他。
谢宴察觉自己快到了的时候,将她向后推倒,他双手抓起她的乳,不带任何怜惜地蹂躏。
身体传来的痛苦让陆行焉必须集中于这场性爱之中,她握住谢宴的手腕,不知是要推开他,还是把他更用力地按向自己。
一股冰凉的液体射入她体内,凉薄的触感令她颤抖,她眼前一片白,短暂失去意识,只由快感主宰身体。
谢宴满足的舔吻着她高潮过后的身体,乳尖在他手指的玩弄下变得坚硬,他用鼻尖蹭了蹭,又一口含住。
陆行焉的腰不受控制地弹起,谢宴的手正好穿过她的腰下,将她翻成向下的姿势。
重新翘起的阳物在她后腰这段曲线上来回摩挲,他伸手探向她方才被疼爱过的地方,湿的一塌糊涂。
他再次入进去,有了第一次高潮后的润滑,这一次很顺利。
她的阴穴是世上最温暖的地方,比她的怀抱还要温暖。
谢宴不舍得一次就入进去,所以他刻意放慢速度。
一切都被放慢,感官被放到无限大,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她都能感觉到。
她是如何被他撑开,又如何热切地吸吮他
陆行焉都感觉得到。
滚烫的胸膛覆到她的背上,不知何时,谢宴将二人的衣物都脱光。
纵使从年少起,这两张身体就常常交缠在一起,可彼此赤裸地接触,还是头一次。
谢宴双手将她双手扣在耳朵两侧,二人的身形完全重合。
他这一次入地很温柔,令陆行焉想起关山的时候。
那是她人生第一次被人爱,被人用温柔包围。
她颤抖着喉咙问:“谢无咎,你爱我吗?”
“你说的没错,我不爱你,我只当你是个玩具,想要占有你而已。”
没有爱是一厢情愿的,也没有爱是会伤害对方的。
他报复着说道:“我恨你当年离开,所以利用你去杀谢欺山,又恨你把谢欺山当恩人,所以才想要你因为你是和谢欺山有关的人,我才想要你。”
陆行焉听罢,也只是苦涩一笑。
是呢,只是个玩具。
“不过,你也不在乎的不是么?”
谢宴在她体内再一次高潮,阳物半软,却仍留在她身体里。
陆行焉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在此时尤为可笑。
她心平气和地说:“如此最好了。”
谢宴自嘲地一笑:“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怜?一辈子像个傻子被人玩弄”
“不是你的错”
他怕她会说出可怜他的话,立马捂住她的嘴。
“你不恨我倒也好,就连我都恨我自己没人不恨我吧。”
陆行焉想说的话,只能吞回腹中。
陆行焉·谢无咎(大结局)
天色渐亮,陆行焉在谢宴怀中醒过来,两个人的身体赤裸地抱在一起,毛毯从他们身上滑落,覆盖住的部分仍紧紧连接在一起。
窗外一片洁白,没有任何事物的侵扰,世界安静无声。
这样纯净的光景,是谢宴最喜欢的。
陆行焉挣不开他的怀,就静静看着落雪。
她已错过今日晨练的时间。
抱著她的男人仍在梦中,即使这样,他也蹙着双眉。
她抚过横贯他脸上的那一道疤,心中隐隐作痛。
这道疤划破了他的少年意气,也划破了他的心吧。
他的心长什么样子呢
应该也是有很多创伤的。
谢宴睁开眼,看到她湿润的眼,不禁觉得讽刺。
每次,都非要他变得狼狈不堪时,她才舍得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
再可怕的疤痕,也不会令他这双漂亮的眼睛蒙尘。虽然他眼中的星辉不再,可深入寒渊,更易让人沉沦其中。
陆行焉收回自己的目光,道:“你要不要剃须?看上去老了很多。”
“不觉得这般沧桑更有风韵么?”他自恋地摸着下巴上的胡子。
现在她面前的这张脸,大抵就是她曾揣测过那张面具下的脸。
奈何府的宗主,和她的谢公子,两张脸在她面前重合成一个完整的谢无咎。
“总是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她低语道。
“阿九,若当初在关山你遇到的是现在这张脸,还会和我下山吗?”
不是谢欺山的脸,只是属于他谢无咎的脸。
陆行焉不知道答案,她从不追究已经发生过的事。
她无措地摇摇头,情爱之事上,她从来不开窍。
谢宴手抚在她光洁的肩头,哈哈笑道:“就知道你是个易被被美色迷惑的女人。”
陆行焉一巴掌拍向他手臂:“才不是这样。”
她愤恨地转过身,谢宴的胸膛立即贴过来。
“不过你已经拥有过这世上最英俊的男人了,是不会再被其它人迷惑的。”
“谢无咎,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哪有人自恋成你这个样子的。”
“正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像我这样,我才是独一无二的。”
若不看那张失去少年意气的脸,只听他的语气,犹是关山那个不可一世的少爷。
陆行焉枕在他手臂上,宽厚的肩膀是她可以依靠的高山。
年少不知事时,恨他、怨他,也依赖他。宗主是巍峨的,他侵占她的领地,却也保护着她。
那时万事依赖着他,只要宗主在,魍山陵的大风都不可怕了。
当初她心目中那个如山一般高大宏伟,可以抵挡一切的男子,也不过是个少年。
“我有事要找谢欺山,晚些时候回奈何府找你。”
谢宴出发前,轻佻地拍了拍陆行焉的脸颊。他又想,其实自己回不回来已经无所谓了。
他不爱陆行焉,陆行焉也不爱他。
这求而不得的游戏,到此为止。
他又添了句:“你不必担心谢欺山,我还不至于为难一个快死的人。至于你愿不愿意等,都随你。”
陆行焉不是会挽留人的性子,而且,谢宴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她没必要干涉。
她只需要把奈何府打点好了,把谢侯府的烂摊子给处理了,让他有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
她叮嘱:“谢欺山不能见风,你不要带他去外面。”
他最恨她提谢欺山三个字,本想好好告个别,这下是非得给她点厉害。
谢宴忽然杀出一个回马枪,点住陆行焉穴道,一手紧揽她的腰,另一手探入她裙底,在她阴穴中搅弄。
她的心未必是自己的,这处必须是。
陆行焉的内力已经全部恢复,趁她重开穴道给他一巴掌前,谢宴主动解开她穴道,坏笑着逃离。
陆行焉看着他溜走的背影,狠狠朝树上拍了一掌,枝头仅剩的几片枯叶被震落而下。
谢宴赶到疾青山,正巧撞上大肚便便的萧声声。
萧声声见到他,立即进入护雏的母鸡状态。
他不耐烦地冲萧声声皱眉:“滚开,要不然连你肚子里那个一起收拾。”
萧声声转头就跑去给谢湮通风报信。
谢湮抚了抚她肚子:“你这么冒冒失失,怎么当娘亲?”
以后萧声声不止要照顾她自己,还要照顾小的,他实在不放心。
“公子,谢无咎来了。”
“怕什么?他是我弟弟,不是恶鬼。”
萧声声知道谢欺山不愿听人说他这个弟弟的不好,她只敢在心里小声咕哝:谁说不是恶鬼?
谢湮勒令萧声声去休息,自己披上披风,去前庭见谢宴。
谢宴今日只穿了一身黑衣,倒是朴素。
谢湮问道:“可需要我去请母亲来见你?”
谢宴翻个白眼:“还是让她去做她的春秋大梦吧。我是来找你的。”
双生子虽注定相杀,可是,他们之间仍有只属于双生子的心灵感应。
谢欺山有预感,谢无咎回来找他。
“跟我去一个地方。”谢宴的口吻不可一世,不可抗拒。
谢湮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宜随处走动,可是,他不想在谢宴面前服输。
他不是明天死,就是后天死,不是今年死,就是明年死。
没什么好怕的。
他都不问去何处,就直接应了:“好。”
谢宴心中想道,谢欺山可真是命比纸薄,自尊心比护城墙还要厚。
风雪刮了一路,双生子行了一天一夜,来到春秋关。
春秋关已远离中原的平谷,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苍茫大漠被白雪覆盖,像是无人踏足过的雪原。
谢湮此生从未见过这样的大雪。
他从马车里走出来,置身满天飞雪中,冷风刮擦着他的皮肤,这是他第一次感受真正的寒意。
以往的冬天,他都被关在四处是火炉的笼子里。
原来这就是寒冷。
谢宴倚靠着马背,双臂抱于胸前,无聊地看着谢湮感受着风雪。
他心中生出一个恶念。
谢宴魔鬼般诱惑的声音到谢湮耳中:“谢欺山,你冷不冷?”
谢湮轻笑道:“虽则冷,感受却很真实。”
“那就让你感受更深刻一些。”
谢宴从地上捧起满手雪,灌进谢湮衣服里。
刺骨的冰冷激起谢湮骨子里的反叛,他将谢宴扑倒在地上,摁在雪中。
论打架,除了陆行焉,没人是谢宴的对手。
他立马翻身压住谢湮,把他的脸扣进白雪之中。
谢湮去踢他膝盖,谢宴条件反射地弹开,二人在雪地里扭打起来,势必不要对方好过。
直到最后筋疲力竭,才双双躺在雪地中。
谢宴打架打得口干舌燥,抓起一把雪灌入嘴里。
雪水在他口中融化,比他以前喝过的任何甘露都要清甜。
谢湮不能在外太久,他默默站起来,沮丧地独自回到马车上。
他望着谢宴躺在雪地里的身影,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求生欲。
若他能像谢宴那样肆无忌惮地躺在雪地中,若他也能游历山河
风吹过,二人存在过的痕迹很快被掩埋。
纯净的大地上,谁都不曾来过。
谢湮的身体熬到了年底。
萧声声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她开始白天琢磨给孩子起什么名,晚上担忧自己会不会诞下双生子。
她几乎没空去想谢湮何时会离开自己。
不知胎儿是男是女,是独子还是双生,谢湮迟迟未起名。
疾青山开春,陆行焉上山来看望他们。
萧声声拉着她的胳膊埋怨:“阿九,你快帮我孩子起个名好不好?谢欺山烦死人了,让他起名字,迟迟不肯起。”
陆行焉伸手抚了抚萧声声的肚子,和颜悦色道:“怎么能是我取?公子心中定有他的打算。”
“哼,他什么打算,我还不清楚吗?”
谢湮的筹算,萧声声心中清楚,陆行焉心中也清楚。
萧声声吃罢饭就去午睡了,陆行焉将自己给孩子准备的贺礼交给谢湮。
是一对纯金的长生牌。
陆行焉道:“也不知是生一个,还是生一双,我就命人打造了一对。”
谢湮打趣道:“对你来说可真是大手笔了。”
陆行焉问他:“公子是在等谢无咎给孩子取名吗?”
“他是孩子的亲叔叔,以后,孩子也要依赖着他由他给孩子取名再合适不过,若是生一双,正好他取一个名字,我取一个名字。”
谢湮刚说完这番话,他身体忽然僵住。
血液在他体内剧烈翻腾,随着翻腾,他的血被一点点净化。
他的心脏狂跳不止。
这是他第二次有这种感觉。
第一次,谢宴受重创,多年来死蛊第一次离开谢湮的体内。
生死蛊,双生子,一方死,一方生。
谢湮手中的一对长生牌滑落,他望向陆行焉的方向:“死蛊从我的体内离开了”
死蛊不会生,不会灭,只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谢无咎生,谢欺山死。
谢欺山生,谢无咎死。
陆行焉突然被抽走浑身力气,她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任何事物。
她失神地回到奈何府,新年的热闹,人声沸腾,全都和她无关。
此时,新入奈何府的小童给她递来一张红笺。
她翻开红笺,只见红底暗金纹的背景上,写着两行漂亮又有力的字:
陆行焉,谢无咎。
屋外大风吹起,再也无人想她。
写在最后的作话。
等番外写完了再放上来吧。
这是个漫长的,关于陆行焉和谢公子,陆行焉和谢宴,陆九和谢宴的故事。
长篇可能有些节奏太慢,后期也有读者说看不出两个人的感情。但乱山就是慢悠悠啦,两个人的感情在关山和疾青山的风声雨声里。
阿九不是无情无欲的孩子,而是她的情欲,她的一切都是和小谢有关的。虽然也心疼小谢,但还是心疼阿九更多些吧,小谢活着,有家人,有仇人,有怨恨(虽然最终证明他被命运玩弄而已),但阿九的所有爱恨情仇都只属于一个人,他是她心中的老师,是教她的恩人,是丈夫,是仇人,是爱人,没了陆行焉,谢无咎还有活下去的理由,但没了谢无咎,陆行焉什么也不是。
陆九vs谢宴,陆行焉vs谢公子都是be了,番外是只属于陆行焉和谢无咎的圆满。
至死方休的纠缠,就是初恋吧。
更多圕籍請訪問:ΓǒúΓοúЩú(肉肉剭).οΓɡ
陆行焉·争夺
同类推荐:
糙汉和娇娘、
快穿之女配势要扑倒男主、
闷骚(1v1 H)_御宅屋、
乱交游乐园、
她见青山(婚后)、
学长的诱惑_高h、
顾家情事(NPH)、
今天你睡了吗[快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