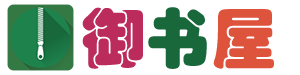虽然在一众乡徒们面前摆出一副慷慨卫道者的姿态,但想到接下来的布置安排,翟慈心内仍是充满忐忑。
县署周围虽然聚集了上千名乡勇力卒,但翟慈仍是一副坐卧不安的模样,视线频频望向一脸平静端坐的王猛,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说道:“景略,此事究竟有几分把握?”
王猛转头望去,翟慈老脸上则浮现出几分局促并羞赧:“我、我也并非怀疑王师战力,也不是忧虑自身安危……生于此世,活到这个年纪,已经算是侥幸偷生,若、若今次真能令乡土从速入治,儿郎不再受战乱所害,纵死又何惜。只是那游氏乡贼实在势大,我、我只恐此事再生变数,祸我乡土更多……”
“我与明府同往,成则共荣,败不偷生。”
王猛开口回了一句,语调仍然平静,心中却不免一叹,更感于自己的能力不足:“尽于人事,恭候天命,若苍天果然垂怜此乡,明府此番大义涉险必不虚掷。”
翟慈听到这里,便是哑然一笑。他年纪比眼前这年轻人大了一倍有余,经事也多了数倍,但若讲到从容静气,却还远远不及。
再一想到这年轻人不过行台先遣一名微卒,此类英流少贤于天中不知凡几,更难想象那位沈大将军究竟何等人物,竟能招引如许多的世道贤流供其驱用乃至不惜以命相报。
一念及此,他心里便不由得踏实许多,口中也忍不住叹息道:“陋居此乡,所见尺天寸地,若非景略入此教我,更不知天地苍茫之大。幸为行台拣取,能够传道荒土,实在此生大幸!”
此时在金氏陂北,作为翟慈乡境宿敌的游秩心情也是忐忑不安,只是他并不如翟慈那般幸运身畔还有一个王猛可以予之安慰。
此刻坞壁中虽然亲徒也都环绕在侧,但一个个望去比游秩还要更显仓皇无措,这不免让游秩心情更加烦躁,顿足怒斥道:“往年家业不是无危,哪一次不是并力却敌,安渡至今!晋军错眼,扶助翟氏狗贼,但其军也并非全无苦恼,又能作几分施力?翟贼若果真敢犯我,灭族之日不远!”
言虽如此,但游秩心内不安却越来越浓烈,坞中两百余骑兵,是他手中最强力量,此前派出近百骑于乡境周边搜索那一营消失的弘武军,最开始还频频有消息传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消息传递回来的频率却越来越缓。
当然这也是正常现象,金氏陂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地势宏大的战场,但南北纵横也达几十里,且地形复杂多变,单凭区区百数骑是很难滴水不漏的耳目严控起来。随着探索的范围越来越远,消息传递自然也会渐渐困难起来。
只是,上一次消息传回已经有多久了?似乎是说已经发现了确凿的敌军踪迹,正在加紧追赶逐杀。
虽然对于直接对晋军下杀手还有几分忧忌,但眼下也顾不得这么多,很明显晋军是打算帮助翟慈老奴来为难自家,无论未来如何,还是要先渡过眼前危机再说。
太阳渐渐自天中向西面偏移,游秩心情也越来越烦躁,已经不能安坐室中等候消息,索性登上自家坞壁望楼,眼望向坞壁外苍茫原野,皱眉问道:“还无消息传来?”
“两个时辰前尚有讯息,但至今还无……”
“已经两个时辰了?”
游秩听到家兵回话,心内已是悚然一惊,下意识昂首望向天际,只见那日光边缘已经明显出现了黄昏晕色,他眯着眼仔细观望,竟从那晕色中窥出几丝血线!
“再探!再派五十……三十骑出堡探望。”
心头那种不安越来越难以按捺住,游秩语调都带上了几分沙哑:“只准他们远出十里,无论有无消息,日落之前必须返回!”
很快,坞门便被打开,又有三十骑飞奔而出。那急促的马蹄声让游秩心情略归安定,他家虽是乡境一霸,但想大批量的供养战马也是不可能,因有战马的限制,所以能够选为斥候的子弟也是精益求精,每一个都骑**湛、技艺不凡,完全不逊于那些真正的军伍精锐。
那弘武军或是天中强军,但毕竟只是一众走卒,即便是再怎么精勇,又怎么能够对这些纵马奔驰的儿郎健卒造成威胁!这是行伍军阵中的死规铁律!
莫非年纪大了,便自然胆怯起来?
游秩嘴角泛起一丝讥笑,不知是在讥讽自己太过紧张,还是讥笑翟慈狗胆包天。
人在焦急的情况下,时间会过得非常慢,但无论快慢都是错觉,夜幕仍然如期降临。阴霾自天际垂落,不独覆盖万物,更渲染到了游秩的脸上。这段时间里他始终站在望楼上,竖耳倾听,可是直到天黑,郊野都没有再响起马蹄声!
“怎会、怎会如此……怎么会?”
他口中喃喃细语,视线茫然的望向身边卒众,然而凡其视野所及,兵众们俱都下意识的垂首避开其视线,无形的恐慌已经在每个人的心内泛起。
“那些晋卒倒是生得一副好腿脚,竟然蹿出了那么远……”
游秩强笑一声,继而抬手攥住身畔的横杆,口中发出冷厉的声音:“家业世立在此,谁敢害我,都需拿命来换!”
“火、火……”
他话音刚落,身边突然响起颤抖的惊呼声,继而转头望去,东北侧夜幕下一抹火光正拔地而起,侵入夜色中!
眼见此幕,游秩胸腔陡然如蛤蟆一般膨胀起来,沁凉的夜风灌入肺腑之内,让他渐渐恢复些许理智,只是背部下意识的靠在了楼柱上。
火光很远,最起码距离他家坞壁很远,只是那方位、那……
“王家,已经被攻破了?”
口中虽然是疑问,但肺腔里灌入的气息却变得虚弱无比,听起来更像是一种陈述的语气。
王氏坞壁在金氏陂下,距离游氏坞有将近二十里的距离,地近泾塬,自二十多年前便依附游氏,但本身也有将近两千家众、五六百的壮力,甚至今次还派来近百家众帮助游氏守坞。
救不救?
游秩心内生出这个疑惑,但还没有做出决定,便听到望楼下坞壁内已经响起了嚎叫喧哗声。其中一个粗豪的声音尤其刺耳,游秩一听便辨认出那嚎叫者乃是他家婿子,也是王家儿郎,正大叫着让人打开坞门,他要夜奔救难。
对于这个颇为勇壮的婿子,游秩也是多有喜爱,尤其在得知丈人门户将要遭难,其人便率领家众来援,更让游秩感怀诸多。
可是很快,他口中却发出冷厉之声:“此必敌人蛊惑阴谋,速速押住八郎!谁若再敢喧扰滋事,就地斩杀!”
家众们领命下楼,继而喧哗声便陡然又响了数倍,但又很快归于平静。望楼上,游秩已经穿起了甲衣,手中握住一柄战刀,凝神望向北面火光方向,眼见着那火光继续壮大,达致最盛处之后便渐渐收缩,仿佛被夜幕所挤压,渐渐缩成一点微光,仿佛天际星斗垂落在了原野上。
游秩微不可查的松了一口气,只是这口气还未完全透出,突然卡在了喉咙唇齿内,因为在那已经熄灭的火光另一侧,突然又有一团火光冒起来!
不得不说,游氏能够霸居乡土多年,的确是有其所恃。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一次的火光冒起并没有在坞壁内引起什么骚乱。
甚至午夜后的第三次火光冒起,同样也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只是每个人都隐隐觉得,笼罩在周边的夜幕更浓厚了几分。哪怕站在篝火旁,确凿感受到那火光热度,一旦视线离开了火光,视野便被黑暗填满!
这一夜注定是一场煎熬,哪怕没有游秩的命令,坞壁内众人也都没有丝毫的睡意,一个个挤在坞壁墙头上下,周遭传来的拥挤并杂乱的喘息声,让他们得以安心。
再难熬的一夜,天明总会到来,不知不觉中,夜色渐渐消褪,而那些待命竟夜的兵众们也都渐渐麻木、继而疲累难当,不乏人已经互相倚靠着频频低头瞌睡。
甚至就连游秩后半夜的时候也蜷缩在了望楼里睡去,身边两个儿子一前一后臂撑着老父身躯,眼眶里满是血丝。
“野中……那、那是,有敌众!”
突然一声尖叫响起,打破了这片静谧,而后城头上下顿时响起一连串的骚乱声。
望楼上的游秩也陡然惊醒,甩甩仍然有些昏沉的脑袋,继而便一跃而起,瞪眼望向郊野。
黎明的原野上,光线仍然稀薄,依稀可见一线黑影正向坞壁方向游动而来。
“儿请外探敌……”
游秩的另一个儿子开口说道,然而话讲到一般,游秩却如被毒虫蜇了一般陡然原地跳起,语调则带着一股就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惶恐:“不可、不可,静待……”
敌人前进的速度并不快,但是随着野中光线越来越充足,敌军全貌也渐渐展现在坞壁城头众人视野中。
那是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约莫只有五六百人,阵型也非常松散,在这荒凉晨景下望去甚至有几分可笑。
待到一点金光冲出天际,那支队伍也来到了坞壁外里许距离,隐隐已经可以辨认得出,排在最前方的那个骑在马背上之人正是翟慈。
“老贼所率寡弱之卒,夜中故弄玄虚,天亮后便劣态毕露,莫非想以此不堪之众破我强坞?”
游秩眼见这一幕,脸色都气得隐有扭曲,指着城下那稀疏卒众,口中则发出略显夸张的笑声。
城头上一众游氏家众也都明显松一口气,未知最是恐惧,他们昨日派出斥候踪迹、消息全无,令他们对外间一切都无所知,夜中又接连起火似乎后路坞壁被次第攻破,更让他们惶恐于不知将要面对怎样强大的对手。
可是到了白天一看对方原形毕露,心头一颗大石落地,继而便因昨夜之惊惧而敢羞恼,一时间请战声不绝于耳。
敌军弄巧成拙,士气再次高涨,虽然消失的斥候仍然让游秩心情沉重,但已经全无昨夜那种绝望,但是面对属下们连绵不绝的请战声,他也并未丧失理智贸然出战,只是站在望楼静观事态发展。
清晨郊野寂静,坞壁中敌人们的哄笑辱骂声清晰传来,翟慈脸色也不慎好看,甚至自己都觉得周遭这些乡曲实在是太丢脸了。
其实这也并不是他刻意保全实力,无论在公在私,他与游氏都难两存,甚至都有倾巢而出的决心,但却被王猛所阻止,只是带领这区区半数乡勇至此。
而王猛自然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他手中可用力量实在太少了,千数乡勇还是翟氏、张氏等几家凑起来的。虽然县中吏户激增,但那些人要么是弘武军的战俘,要么是野中流民,非但不能整编战用,甚至还需要留下足够的力量防止他们串结哄逃,能够抽调出这五六百人众,已经算是极限。
且不说翟慈老脸发烫、羞涩难当,王猛却是神态严肃组织这些兵卒们开始劳作,将地面稍作平整,用携带来的竹木器仗搭建起一个不算太高大的平台。
那些卒众们也都不是傻子,行至敌人眼皮子底下难免惶恐有加,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不免束手束脚,随时准备逃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却见坞壁中敌人虽然叫骂凶狠但并不敢出击,不免也渐渐胆大起来,甚至有人一边忙着手头事务,一边开口回骂起来。
整个高台落成,用了足足一个多时辰,在这过程中,双方对骂不已。而在这个过程中,周遭乡野也渐渐出现其他人家部曲,各自远观眺望,并不靠近,一副两不相帮的架势,或者也是存念这乡中二霸相争,趁机捡个便宜。
在这些围观者中,出现一路将近两百余名骑士,这在一众乡徒当中比较引人瞩目,但也达不到令人惊悸的程度。倒不乏人对那些战马流露出贪婪之色,但很快又被游氏坞前奇观吸引了注意力,但也难免有人打算稍后真的打起来,趁乱去抢夺一些战马。
高台架起之后,王猛才亲自上前,将翟慈迎了上去,随同而上的还有多名县署属吏,包括王猛在内。
翟慈也算见过风浪,虽然周遭气氛不妙,但也还是登台安然落座,然后才打开一份卷宗,肃容道:“王道再入关中,县署承命复设,乡野多**猾,今日本署于此设案听讼断狱,惟求秩序再归乡野,生民复归法网!章法即设,刑赏分明,审有罪,褒有德,决断牍案,即刻执行!”
他虽然扯着嗓子嚎叫,但能够传出的距离实在有限,但台下力卒环绕,待其讲完之后,随着一声鼓响,数十人扯着嗓子将其话语原原本本、整齐如一的号叫出来,顿时压住野中诸多喧哗,竟也显出几分威仪气度。
翟慈听完后,脸上也流露出几分欣慰笑容,自觉家中儿郎虽然愚蠢,但也并非不可造就,苦练一夜便有了今夜这种气象,也实在难得。
那些力士们吼叫声自然也传到了坞壁城头,游秩在望楼上听到那吼声之后,才明白翟慈这一番作态意义何在,脸色顿时转为一片铁青,挥拳砸在了栏杆上,口中则咆哮道:“老贼欺人太甚!”
“坞中骑众,速速集结门后!再集五百精卒,一并杀出,我必将这老奴擒杀在此!”
往年乡斗中虽然也有互相辱骂,但游秩却没想到这翟慈老贼居然嚣张至斯,扯着虎皮做大旗不只,居然堵在他家门口说什么要审断他的罪迹!被人羞辱至此,他又怎么能够忍耐!
此时野中那些围观乡众们也都半是诧异半是狐疑,想不明白这个翟慈究竟是老糊涂已经疯了,还是真的确有所恃,居然敢于堵着游氏家门作态找死!
甚至已经有人忍不住率众欺近于前,既为了看得更清楚,也是为了更方面稍后渔利,早一步确定翟慈作死成功,便可先发一步的行动,无论是翟氏坞壁、还是那个所谓下邽县署,都是他们筹算在谋的肥肉。
察觉到周遭异态,翟慈额头上也变得汗津津的,他虽然见惯风浪,但这样刺激的场面却还没经历过。尽管昨夜已经给自己打气良多,但真正发生时,仍然略有怯场。只是看到左侧王猛始终安坐,心情这才又恢复些许镇定。
“刑令之威,在乎五刑,笞、杖、徒、流、死……”
随着翟慈念诵普法,各类刑具也都一一架设出来,并陈平台之下,远远望去,竟给人一种森然之感。而那些平台前的力卒们,一个个挺胸凹腹,壮声念诵所谓的县署刑规,合共三十余条。
乡野中那些围观者初时还只是哄笑,可是听着听着竟然渐渐有了几分正色,甚至不乏人垂首默诵。
这一番普法,持续了将近两刻钟,甚至有数块硕大门板被竖立在了平台周围,上面俱都写满了刑规,一个个字迹庞大,但究竟有多少人能认识,其实堪忧。
“先审罪户胡氏!”
翟慈站在平台上一声断喝,声音经力卒们传递出去之后,周遭乡野也是一片哗然。因为这个胡氏,便是昨夜坞壁起火的一家,之所以周遭这么多人观望,也是因为昨夜那番动静太大,让这些乡人既惊且疑,打算一观究竟。
原本看到翟慈如此孤弱之众,他们已经认定昨夜只是虚态,可翟慈这么一说,又让他们心弦绷紧起来。
乡众们疑惑并未持续太久,随着翟慈话音落定,突然有十几个血淋淋人头被抛出来。围观者们见状,更是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只见那十几个人头被各自摆出,每被提起一个,则有力卒宣告其人所犯何事。
每诵念完一人,便有两名骑卒乘马挑住首级绕行一遭,向周遭展示。乡众们虽然下意识退避,但又忍不住好奇心探头去望,待到依稀辨认出人头模样后,心内更是巨震,原来昨夜那些事的确发生,并非假象!
“杀!杀出去!”
望楼上游秩眼见那两名骑卒居然还敢挑着人头奔向自家坞壁,更是愤怒得目眦尽裂,挥臂咆哮道。
坞壁大门轰然打开,早已待命的游氏骑众并精卒们吼叫着冲杀出来,周遭围观乡众们眼见此幕,也都惶然色变,一个个引众退避,担心遭受殃及。
然而正在这时候,野外旁侧原本阵势松散的那两百名骑众陡然集结成队,散漫荡然无存,如一柄钢枪迅猛扎向冲杀而出的游氏家众。
1216 夜幕杀机
同类推荐:
偷奸御妹(高h)、
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
肉文女主养成日志[快穿系统NPH]、
娇宠无边(高h父女)、
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
彩虹的尽头(西幻 1V1)、
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
师傅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