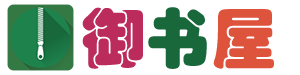纪友早数日前离都,周行过大半个曲阿,终于在曲阿西南一座山谷中见到了张健。
如今的张健较之纪友印象中那个刚毅沉稳的形象已经大不相同,脸色略有苍白,眼神游移不定,须发杂乱,整个人似是颓丧无比。
而其部众也早已经离散大半,眼下尚跟随他的,除了早先被沈哲子击败后仅剩的那百余不离不弃的部众外,便只剩下几百人的历阳本部人马,尚不足千数。当纪友寻来时,这些人还在山谷中绕行寻找出路,似是要翻过山岭往南面去。
“不意还能再见纪君一面,只是如今我这模样,羞见故人,实在有些失礼。”
张健在河谷边的高岗上席地而坐,短短数息的时间里,手掌不断摩挲着膝盖,视线也频频转望向各方,十足一个局促的惊弓之鸟,再没有一点早先在曲阿县内时与纪友坐谈那侃侃而谈的风姿。
“张侯请放心,我今次来随员只有岭下那十数人,并无别部。”
纪友看到张健这幅模样,心中不乏感慨,温言安慰张健道。
张健闻言后挤出一丝不乏苦涩的笑容:“我信得过纪君,我、唉,我是自觉形秽……纪君你这又是何苦?”
“那张侯你又是何苦?世道沧桑,人力有穷,应止则止啊!”
纪友是真的痛心,他沿路行来,所见早先他竭力保全的曲阿已是满目疮痍,诸多恶行令人发指,继而上升到对自己的罪咎。早先他是真不觉张健是这样人,若早知今日之曲阿受害至此,此前他就应该不惜性命手刃张健!
张健闻言后便是苦笑,而后正色道:“若我说曲阿之近况非我所为,亦非我所愿,纪君你信不信?惊闻沈郎奇军突袭,克复京畿,创建大功。惊愕之余,我心已乱,哪敢再为奇谋,惟求能奔袭主公帐下,效死尽忠!所部难束,东扬军驻于近畔如喉中鲠骨,为求脱身,分散部众趁乱而出……”
纪友听到这里,稍一错愕,旋即便是默然。他心知事到如今,张健已经没有再欺骗自己的必要,但若不是张健鼓动那些宿卫乡人侵害乡人,反而让他更加难以接受。
张健见纪友沉吟不语,脸上苦涩更浓,不免又叹息道:“若早知军心如此可用,我何苦要自废部众?事到如今,我自己都已茫然,明明沈郎轻身孤军身入京畿,振臂一呼,投诚者巨万,一朝废尽我等苦战之功!可是到了我之所部,那些宿卫们脱控之后,非但没有驰援京畿,反而各自为战,在乡野中肆虐起来,所害尤深我军。纪君你世居江东,家学渊源,能否为我解惑?”
纪友闻言后更加说不出话来,说实话,此时他心内也是如张健一般迷茫,不知为何会发生如此恶事。
“难得事到如今,纪君仍肯见我,客居江东经年,能得纪君礼厚,于我而言,已是不虚。”
纪友听到这话,心中更加感怀,沉声道:“张侯,随我去见驸马吧。曲阿之祸,非你所为,我信得过你。来日同归,我自为你在驸马面前力争作辩。逆事将败已成定局,你又能去往何方?”
“我又能去往何方?哈,我又能去往何方?”
张健闻言后,那魁梧身躯蓦地一颤,竟透出一丝软弱无力之感:“当年北地遭灾,胡狗肆虐,匹夫挥刀而起,所为者活命而矣。侥幸不死,竟得薄名,乡土不靖只能转道南来。无人是天生的反骨,肃祖明堂之诏,寒伧竟能为国之用,血肉扶鼎,这是怎样的荣幸?”
“屡世寒伧,热血未冷!可是我等保下的是怎样一个世道?内外见疏,上下离心,居官者以猜忌为己任,效力者以门第而见疏!胡虏只夺人命而已,高门却连人志都要抹杀!不得为忠勇之卒,我等除了做逆贼还能做什么?”
“我是极羡慕纪君,还有沈郎这种世家贤逸,才大不虚,家世清贵,壮志可酬!可惜张某一介寒伧,难入高贤之眼,休矣!此生是难活得明白,惟求死得安心!”
讲到这里,张健目中已经隐有泪光闪烁,站起身来对纪友长施一礼:“多谢纪君送我一程,此生已难再见,可待黄泉共歌!转战经年,惟得贼名。此身何惜,本应赠予良友再建事功,可惜主公军败蒙难,不敢言弃!告辞!”
说罢,张健蓦地转身大步行下高岗,率众而去。
————
随着沈哲子的军令发出,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大量原本隶属张健部的宿卫乱军纷纷涌至曲阿县治。
这也是没有办法,京畿已经收复,苏峻又是大败,任谁都知道这一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叛乱将要平复。这些宿卫们要么逃至深山老林此生不出,要么投入大族受其荫蔽,否则只能乖乖回归统序。
不过这些人大概也知道自己所为之事有多罪孽深重,因而少有小部归来,往往都是汇集成数百上千人的大队,大概是人员的优势能给他们以安全感,毕竟法难责众。
“为什么要这么做?”
曲阿县署中,坐在沈哲子对面的一个年轻宿卫将领被沈哲子冷厉的眼神盯得有些不能淡然。
这年轻人不是外人,乃是纪况之子,纪友的堂弟,名为纪昌,也在宿卫之中担任军职。大概是因为这一层关系,单单纪昌领回的宿卫便有一千五六百人。而这一队宿卫也最惹人注目,且不说兵众一个个背负着大量的财货,甚至堂而皇之押运着数十辆载满粮帛的大车,可以想见他们又做了怎样的恶!
纪昌两眼布满血丝,单薄没有血色的嘴唇翕动着,不敢直视沈哲子的眼神。因为沈哲子不只是都督上官,还可以算得上他的长辈。
“你哑巴了不成?难道以为我不敢杀你?”
见纪昌只是满脸惊惧,却不敢开口,想到早先亲眼所见那一幕惨剧,沈哲子更是恨得牙关紧咬,抬起脚来一脚踹在纪昌面门:“敢为如此恶事,你对得住你家先人?对得住丹阳乡人?”
“做得干净,不会外泄……请、请驸马……”
纪昌捂着脸颊,血水已经从指缝渗了出来,语调颤抖不定。
“畜生!你还有脸来见我?你怎么下得去手!”
沈哲子抽出佩剑来,剑锋抵在了纪昌胸膛上。
纪昌低头看一眼那剑锋,身躯已是一颤,继而便悲哭道:“末将该死,死不足惜!但请驸马明鉴,末将从未下令攻破一庄,从未下令害一人,双手绝无沾血,所获寸缕无受!”
“哈!做了这么多恶,你是在告诉我,你问心无愧?你清白如玉?你身为将主,不能节制部众,留你何用!”
沈哲子听到这辩词,已是怒极反笑。
“可、可是末将要如何阻止他们?这些宿卫,大多良家,一条人命便扯出老幼妇孺的一家!他们无奈从贼,已经是断了前路,能得一二财货傍身,那是最好结果。诚然那些乡人也是无辜,可是末将只是庸才而已,能谋者只为同袍身计……若一死能偿此罪,末将死又何惜?”
沈哲子听到这话后,心情更是沉重,将剑甩在了地上,涩声道:“王太保台中已有政令,宿卫从逆者各归乡籍,不入屯所,有功者议功授田。”
“啊……这、怎么会这样?”
纪昌听到这话,整个人都僵在了当场,继而便是涕泪横流,叩首于地悲泣道:“末将计差铸成大错,请驸马赐死!”
“赐死?要杀的何止你一人,外面那些贼卒凶徒,哪一个不该死?是不是要将他们统统杀掉?”
沈哲子听到这话,心中更恨。这些宿卫乱军,敢于如此作恶,所恃者无非法不责众而已。即便是他们确凿无疑的犯下大罪,但只要没有强力的苦主请求治罪,为了时局的平稳,台中也只能将这件惨事按下来,不会再大肆宣扬去论罪。
要知道,如果议罪的话,不只外间那几千宿卫人人该杀,类似纪昌这样的世家子弟其背后家族也难豁免。宿卫多为丹阳乡人,而领兵者也多像纪昌这样出身丹阳各家,如果揪着这件事不放,整个京畿、丹阳都要再次动荡起来!
南渡以来,朝廷的军政重心从来都不是厉兵秣马的准备北伐,而是维稳,保证江东不乱!在稳定这一个大前提下,什么样的过错都可以被原谅!王敦第一次作乱之后风风光光的回了镇所,为了维持稳定!庾**反苏峻祸乱江东,平叛之后照样巍然不动,为了维持稳定!
对于这一个所谓的国策,沈哲子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因为他家就是受益于此!凭他家所犯的罪过,如果不是为了维持稳定,早已经被抄家不知道多少次!
但沈哲子心里一直很清楚,如此为政,即便能够维持一时的稳定,那也是假的!因为这会让人人都觉得,只要他们能够把住这个命脉不失,犯再大的错都可以被原谅。哪怕不需要下去调查,沈哲子也清楚得很,如今吴中、江西乃至于荆襄之间,许多地方豪强那是将他家的转型之路作为一个偶像和榜样去学习的!
0369 法难责众
同类推荐:
偷奸御妹(高h)、
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
肉文女主养成日志[快穿系统NPH]、
娇宠无边(高h父女)、
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
彩虹的尽头(西幻 1V1)、
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
师傅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