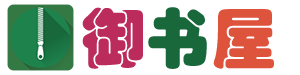侯门纪事 作者:淼仔
侯门纪事 作者:淼仔
第一百七十五章,宝珠不上表凶的当?
这个月的家是侯夫人在管,但老老太太和南安侯夫人相继去世,来往的银钱和送的东西多,二太大和四太太自然是盯着的,侯夫人自然是不服气的,老太太孙氏为了避免办着丧事呢,媳妇们还争执让亲戚们笑话,她也来掺和一脚,管本月的账目。
韩世拓又觉得送辅国公和陈留郡王东西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这份儿东西自然是由公中来出。又有四太太才说过她去守住帐房,韩世拓虽然混,送国公和郡王东西却是件大事情,不能再把吵闹夹在中间,这里面可牵扯到他的前程,就带着掌珠先来见祖母和母亲。
老太太孙氏和侯夫人、二太太三太太坐在一起,说的无非是下葬那天的安排,怎么起棺去家庙,得动用多少人手抬棺,亲戚们看着才认为子孙孝敬,又有多少家人举哀,多少家人跟随,这笔儿钱从哪里出,家里实在没有,就从先收的客人银钱上支用出来。
文章侯府四兄弟不齐心,除了文章侯母子,别人包括韩世拓和侯夫人都是往腰包里扒拉钱的,老太太是母亲,看着儿子们闹,媳妇们搅,痛心却又无力扭转。文章侯身为长兄,不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了这几十年,他左和一把稀泥,右糊一把墙土的,也是管不住家人。文章侯府虽然没到衣食不周的地步,但出来一件大事,如婚丧嫁娶中任一件,再或者宫中要有哪位娘娘过个寿送个二、三千两银子什么的,都有些支用不动。
但外面的排场,一天三餐里每房头各几个份例菜,倒还富足。
二太太想着家里的这些“内幕”,又觉得生气。此时四太太不在,二太太就得自己开口。不过她想说的话,就是四太太在,二太太还怕她说不好,还是自己说的更周密。
“母亲,”二太太阴沉个脸:“怎么就没钱要动用别处的呢?祖母是年高有寿的人,一直病卧在床,这份儿银子就没有早准备下来吗?”
老太太对她也一样的不悦,又加上连天的伤痛,到底是家里去了人。去的那人还在的时候,老太太也怪她偏心,怪她不管女儿。可她真的去了,在女眷们心中是家里少了一大份儿的人。那不是个下人,好歹总是自己的长辈。
又见二太太来纠缠,老太太心中一痛,手捂胸口觉得难受上来,斥责的话就噎在嗓子眼里,停上这么一停。
侯夫人也累了,她是宗妇,应酬上比弟妹们忙碌一百倍。此时听见二太太又有争辩的意思,侯夫人也不想和她再吵,沉着脸也不说话。
现放着婆婆在这里,她不说话,侯夫人想我又何必惹这个城府鬼儿?
是三太太回了话,三太太叹气:“二嫂,为老老太太事存着五千两银子,前年二嫂当家的那个月,二哥出了件事,支用五百两;没过两个月,宫里接连没了两位娘娘,全是有宠的,外面老爷们都说娘娘的外戚圣着高,可是不能冷着,两家加起来又送了两千两银子,又有……”
老太太念佛,她从来佛珠不离手,这就郑重庄严的宣声:“阿弥陀佛,”在心里解气的骂,菩萨有眼,我不驳你,自有别人驳你。
可怜我哪里还有力气和你去辨?
侯夫人也解气,暗想这钱去了哪里,还还是大家一起用掉的,说起来二老爷这一回用的算多的,可他身上有事情,不帮他总不能干看着?
侯夫人总想当个好大嫂,但弟妹们总让她不能如意,不论大事小事就这种大家不服她,她又诉冤枉的格局。
见婆婆念佛,侯夫人也双手合十来上一句。二太太气结,又觉得三太太自从世子媳妇进门后,就不听自己的,恼得瞅住她,势头都对住三太太一个人,直着眼睛问:“好!这钱算是有数了!那我还要问你,姑母是钟家的人,这抬棺的钱和人也要我们出吗?”
老太太忍无可忍,冷冰着脸开口:“老二家的,你姑母的事情一出来,你姑丈当天就来见我,把使用的银钱和人说得清清楚楚。”
二太太说一件事,触霉头一件,又连日也劳累上来,城府也不要了,阴沉也抛开,火道:“他就什么!”
老太太狠瞪她一眼,恼怒着先骂起来:“你姑丈分明是好亲戚,都是让那死去的人害的,又有你们都不约束丈夫吗?以前怂恿你大哥闹的,头一个就是老二!”
老太太不怎么发脾气的人,偶然来上一回冲冠怒,二太太也只能偃旗息鼓,悻悻然先把自己火气压一压,没好气地道:“您老人家又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姑丈他说的话才最要紧不是。”她拖长了腔:“这牵涉到姑母那天怎么动身是不是?”
三太太也没听说过,请老太太快说才是。
老太太叹气:“说起来,妹夫倒真的是个周到人。当天他来见我,对我说以前好也罢不好不罢,但你姑母嫁到他家的,他认的。他说出殡那天,抬棺的人本应该从南安侯府出,摔孝盆的也应该是钟世子,可想到死去的人对他们都没情份,真的全是钟家的人出来,怕死去的人死了怨气还不解,在地上不安宁。”
二太太撇嘴:“他这还是骂我们不贤德呢。”
“你管他骂什么去!他肯管就好!”老太太又要骂,再才冷笑以对媳妇:“回想几十年,又见他这么通情达理的,我知道你们不愧,”
从侯夫人开始,到二太太三太太全红下脸。
“我愧上来,说不必,她的东西全给了世拓,自然件件由世拓承当。你姑丈说他要分担,他出银子钱。”
二太太三太太忙问:“出多少?”
家里每个房头的使用衣裳,都有一辈子的。可外面流动的钱,却从来不足。也难怪她们着急。
老太太伸出手指比了一比,三太太感叹:“这也算好的了,可怜姑丈一生没享过姑母的福,她走了东西也没落下,却还要出这些钱。”
这笔银子把二太太堵得无话可说,她又明知道南安侯不缺钱,出这笔银子只会让南安侯更体面,而南安侯的体面,将又是文章侯府的难堪。
二太太见有钱,还是气怒攻心上来。她不假思索又挑了个刺:“摔孝盆的怎么是钟世子,应该是身为长房的大老爷才是?”
老太太、侯夫人、三太太异口同声反驳二太太:“世子还不好吗?”以后是世子承担家业,世子出面代表的是南安侯府。
再说那大老爸,他肯出面吗?
老太太冷笑:“以前老爷们骂得人家可不轻?”文章侯兄弟不服南安侯妾生子,大老爷是跟着南安侯任上生的,回京后让韩家兄弟到处大骂:“不是我姑母肚子里出来的,这辈子别想上台盘。”
侯夫人叹气,又道:“南安侯府三位老爷全丁忧去官,听说皇上还说了一句,说这兄弟三个人守嫡母之丧,全是贤德的人,还赏赐了东西。”
二太太真正悲愤了。
守嫡母的丧,有长子一个人就行了,犯得着一古脑儿全跟上来。全跟上来,还不是给外面人看的。
你们犯得着兄弟全辞官,显摆着你钟家满门是人,我韩家自然全不是人。
这个对等本身不应该成立,可有以前弹劾来弹劾去的旧事在那里摆着,自然就钟家全是人,韩家都不是人了。
二太太就差恼得一头栽到地上,三太太想想前情后事,也跟着叹道:“不容易啊,换成别人家里,怎么肯三兄弟全辞了官呢?”
这房里的话头儿总和二太太不对,二太太忍气闭嘴。钟家三兄弟辞官又有什么?他们一共四个儿子,大的是世子,二的在外面做外官,因为做外官道儿远,夏天棺木不能等,二爷钟行沛就没回来,七天的功夫,马也跑不过来。
第三个第四个,全是科举上有名的。他们还愁什么?腾出地方来让儿子们也应当。虽然皇上才不会这样做,你们家腾出来的官,给你们儿子当。
但二太太一肚子的怒火,不让她发泄发泄,她离晕过去就不远。
难得有片刻的安静时,韩世拓和掌珠夫妻上来,把送礼的事情告诉一遍。所有的人都是愿意的,二太太更气得怔住,心想他们又攀上了郡王。她想到自己丈夫年前年后打点做外官,苦思外路的郡王没有一个是熟悉的,公文上来往倒有,那公文也只是发给郡王的书吏,再由书吏回复。
这求不得的郡王,现在又成了世子媳妇亲戚的亲戚,可把二太太又气了一回。但这是正经事,却又没法子驳回。说到底,世子和郡王相交,对全家都有好处才是。
至少上门去见郡王,也算熟悉的人。
二太太就不说话,也不帮着出主意,只听着他们在盘算送什么。见说来说去总不合适,二太太嗤嗤冷笑,正想说句压乾坤镇局面的话。掌珠不疾不徐开口:“依我说,是我的亲戚我知道。四妹妹交待我,绝不是送金的玉的古玩宝贝,不过是亲戚进京,不走动总不合适。”
“是是,”从老太太开始,先喝声彩,都听着掌珠说话。
这风头儿转向掌珠,二太太由不得眼前一黑,恨掌珠冒尖才是。
“结交外臣,本是不妥当的。现在是亲戚,才不会有人说。送的东西贵了,我们家现在有事情,从哪里出这一份儿合适?又让御史们拿住把柄,我妹夫现就是监查御史,让他为难可是不好。”
侯夫人点头欣慰,难得的觉得自己娶了一个好媳妇。
“再说那金的玉的,郡王家里还能没有?”掌珠挑起眉尖:“不如送上两桌子上好席面,捡他们在外面吃不着的东西让人做了来,让个妥当人送过去,再说我们家里有事,他们难到不知道?说我们不能去陪,这个不又省钱,又好看,又不会让御史们看到难过?”
老太太喜笑颜开,侯夫人也笑容满面,三太太连说:“好好,”就是二太太听说不怎么花钱,也没注意到家里人全有了笑容——家有丧事,真不应该。
这就让人去备办,把这事儿交给掌珠去办。掌珠撇嘴:“我不敢去?”韩世拓配合的阴着个脸。老太太侯夫人都问:“怎么不敢去?”韩世拓冷笑:“帐房里有虎,母老虎!”掌珠把脸儿扭到一旁,不说话装生气。
老太太就明白了,气得往外面喝道:“把那不省事的人给我叫过来,我说我们全这儿议事,她半天看不到,原来又去帐房!这个月轮不到她管,她不是她站的地方!”
见老太太生气,就有一个人飞快过去,把四太太好哄着出来。四太太一怒出来,气势汹汹地往里走。在亭子下面,见对面路上来了三个人。四太太眼睛一亮,出气的这就来了!
她双手叉腰,避到亭子后面,好整以暇的等着那三个人走过身边。
文章侯府一般儿也有新红初绿,但在黑白灵堂中间,总是灰色而沉郁的。邵氏一边走,一边为这府里难过:“看看这石榴花就要开过季,可怜掌珠也没功夫赏玩。”跟着女儿住的邵氏也是素淡衣裳,不肯用金首饰,全是素白银簪子挖耳,好似也给这个家里守着孝般。
花在她后面抱着衣包,就要出门,花喜欢得有些蹦跳。见二奶奶的心总在这个家里转悠,花就想打掉邵氏这个心思,道:“我们就要去做客,四姑奶奶家里来了贵人亲戚,接老太太三姑奶奶三奶奶一起去,自然也请了咱们,老太太又让人来接您,还管这个家里做什么?”
后面那个,是安老太太打发来接邵氏的人。安老太太想的周到,想袁家是喜事,韩家却是丧事。邵氏一定是穿素衣的,但去宝珠家里又不合适,还是接到家里换过衣裳再去的好。
邵氏也笑了,她能出去散散心也觉得不错。想想宝珠的福气,邵氏为她喜欢,又道:“这有福气的人,都是心平气和能平静的,我的掌珠要是有宝珠一半儿有福气,那就好了。”
花就吃吃的笑。
四太太一蹿出了来!
走在前面的花先吓了一跳,随即板起脸,奶奶才说心平气和的人有福气,这就出来一个不和气的。
花本能地问:“四太太在这里做什么?”
四太太冷笑,眸子却直视住邵氏。文章侯见到尖酸刻薄的四弟妹都是怕的,何况是软弱出名的邵氏。邵氏吓了一跳,往后面退时,又见到安老太太派出来的婆子在身边,邵氏在女儿府上受足气,也不肯让自家婆婆知道。
她就挺挺腰杆儿,怯声怯气地问好:“您这是忙什么呢?”四太太满腔怒火,不留情面的往外撵,她阴阳怪气:“我能忙什么!我就操劳,也落下到死人钱!”细腰一扭,杨柳摆风般目不斜视走开,又甩下一句话:“急着走什么!自家里又不是坟坑台,塞个女儿进来,就跟着撵来。哎哟,这家里难怪花钱多,主仆可花用不少。还有我们家的死人钱,你走了一会儿死人伸出手撒钱,可少了一份儿?”
邵氏一怔,随即泪水盈眶。花“呼”地转过身子,四太太话里把从安老太太到掌珠大姑奶奶全羞辱了,花听不进去。正要回上几句,却见四太太脚步儿快,早走得不见踪影。又有邵氏自己气苦,却反让花走:“别理会她,她心里也苦。”
花气急要跳脚:“她苦,别人不苦?”邵氏让她这样一说,泪水哗哗的往下掉,哽咽的说不出话。后面来接的那个婆子,因为这是别人家里不好插话,就劝道:“快走吧,老太太等着,四姑奶奶等着,好酒好菜好果子,还有那贵人王妃只怕也等着呢,”
花主仆就不敢耽误,急急出府上车,往安家换过鲜明衣裳,出来去袁家。宝珠果然是等着的,贵人王妃果然也早就在。
郡王妃每天得来陪母亲,乍一看上去,就成了等着的人。邵氏觉得体面上来,这脸上渐渐的又光彩回来。
……
家里虽然请客,袁训也回来的晚。大门上下马,见星月早上来,几点碎星光在石阶上闪动,袁训吁一口气,和他每天回来想的一样,宝珠在作什么?
他离京的心越重,想宝珠的心就越多。把马交给顺伯,顺伯照例问他:“小爷,今天衙门里有什么事情?”
袁训就每每地笑:“顺伯,哪能天天出事情?我那是监查衙门,天天出事还了得?”顺伯得到这样的回答,也欣欣然有了得色,为袁训把马牵进去,把大门关上,目送着小爷去房里,顺伯把马往马棚里牵,就自言自语:“要是老国公老夫人见到小爷这样的出息,该高兴成什么样儿?”
这个看似不动感情的老人,背着人就用袖子拭眼角,那里没有泪,却有一处湿润:“监查御史,看小爷多能耐。能查官员,能什么都查。以前跟着老国公当差,以老国公之尊,对监查御史那毛头小官员也是客客气气不敢怠慢,”
又一跺脚埋怨自己:“看我!我家小爷如今当上这官,这官可就不是毛头小官员,正七品的官员,嗯嗯,大官儿大官儿。”
这位前辅国公的亲随,在山西三品以上的官员从来不放心上,此时拿个七品官,自己絮絮叨叨自语着:“这官儿不小,好大呢。”
大小全是袁训自己挣来的,虽然他安置在都察院,太子殿下出了不少力,但读书中举却是袁训自己的本事。
袁训走到正房外面,就放悄脚步。和宝珠每天捉迷藏逗乐子,出其不意的回家出现宝珠面前,是袁训最爱干的事情。
很多夫妻成亲前不认得,成亲后相敬如宾,远不如这一对小夫妻恩爱喜乐。
表凶凑到门帘子上面,他耳朵尖,隔帘子就能猜测出宝珠在正中那间坐着,还是在里面窗上扎花儿。
舅父姐姐一家人进京,把宝珠忙得不行。怕他们吃上先不习惯,每天宝珠都和忠婆做好吃的送去。小外甥们夸舅母扎的花儿好,宝珠又赶着给他们做衣裳绣帕子。小小的念姐儿抓住舅母的帕子就不丢,宝珠就全送给了她。
想到这里,袁训也有得色。看念姐儿才会走路,腿软着走不好,见天儿奶妈抱着,也知道舅母的手艺好。
耳朵里传来低语声,原来红花在房中。
“花对我说,韩家四太太刻薄二奶奶,可把老太太和奶奶您全扫进去,花气呢,要和四太太斗上一架,偏又要往咱们这里来,就没理论她。”
袁训听上一听,宝珠在哪里受了气?就揭帘子进去,笑道:“我回来了,你们主仆在谈论些什么?”宝珠果然是从窗下起来,旁边高几上摆着小小烛台,上面一根红烛。她家常穿着杏黄色绣荷花儿的罗衣,碧绿色裙子,起身亭亭难描难画,和红花过来接住袁训。
宝珠不瞒袁训,帮他解着汗湿的衣裳,道:“说二婶儿在文章侯府里受气?”袁训明知道这与邵氏软弱分不开,还是故意地道:“大姐姐那么刚强的人,二婶儿也会受气?”
红花殷勤送上换的衣裳,就行个礼就要避出去。袁训叫住她,满面笑容:“红花,今天背的什么书?”
红花就背给他听听,袁训就要乐:“好,明儿再用功些。”红花也觉得得意上来,这就出去,脚步儿快的溜进耳房,洗浴用的水在小爷下值的时辰就备下,不时加热水。红花摸摸水不用添换,怕小爷脱了衣裳就要过来,又急步回她房里,见到桌上摆的书,夜风轻送不住煽动书页,红花幸福的叹气:“红花上辈子一定烧了高香,才遇到奶奶和小爷这样的好人家。”
小爷回来,都要和奶奶玩上一会儿,这一会儿不要红花,她点上红烛,继续看书去了。
房中,宝珠在回袁训说掌珠要强的话,宝珠半嗔半怪:“看你说的,不管是什么人,她能保住自己不受气?”
“也是,糊涂人可多着呢。”袁训语带双关。
宝珠明白过来,就笑了:“我知道呢,我不和韩四太太生气。但就是忧愁二婶儿可怎么好?”袁训又意味深长:“二婶儿自己有家,偏要住到别人家里,受气也应当。”但是他安慰宝珠:“反把我的宝珠也带累进去,小宝儿你别气,我今天不叫你小呆子,赶明天再叫。”
宝珠咕咕地一笑,在袁训身上拧了两下:“我才听到受气的话,你也来气我?”烛光下,袁训已解得只余里衣,命宝珠拿上换洗衣裳,怕宝珠害羞又不肯跟去,拖着宝珠往耳房里去侍候,边道:“我是养老女婿吗?这话我早就想说。祖母还在,二婶儿不想着好好侍候,去什么大姐家住?本想等我闲了,闲了我把你家姐丈叫过来骂上一顿,让他撵人才好,那边倒有一位太太帮了我忙,这恶人让她当了,我权且夸夸她吧。”
宝珠笑,又要拿自己花拳绣腿打他:“我本来是气的,你说了这一大通,倒成了让你指使的人,也罢,我不和她生气了,是你说的,糊涂人到处都是,我犯不着一般儿见识。”抬眼,见袁训脱得光溜溜,宝珠吃吃地笑,避开眸子。
“看你,难道没见过,再多看几眼,以后……。”袁训本来想说过几天就看不到,话到嘴边总算及时咽下。还没有走,何必招惹宝珠哭泣。把话收好,扯住宝珠不让她走,哄着她给自己洗。
宝珠随便洗了几下,夺手笑着回去。在门帘子外面交待:“水凉了就叫,知道没……大热天的也不能受了风才是。”
“我又不是泥捏的,”袁训笑语飞出帘子,坐在热水里面的他,见不到宝珠,就没了笑容。微拧起眉头,袁训想姐丈的拒绝在他意料之中,他还有别的法子。不过那法子用出来,只怕娘娘要震怒,太子要大怒,舅父要生气,姐姐要伤心,姐丈呢,因为他现在京里呆着,多少要牵扯进去挨几句说,母亲那里,倒是几年里不断的劝说,她还能答应。
最后再来,袁训皱眉,宝珠要没完没了的哭泣才是。
要宝珠答应自己离开她,袁训猜想宝珠可以和自己拼命。惹急了呆子小宝,就不再是小猫咪,要成小母老虎。
他把水撩得哗哗响,心想还是不早说吧,早说了一堆人出来拦。这一回再让拦下来,可怎么才能学外祖父呢?
袁训生下来时,前辅国公夫妻都早去世。可袁训在当地长大,外祖父的事迹没少听说。他无奈于舅父武将转文职,这种无奈促成他早早的就想驰骋沙场,无人能劝回头。
洗了一回,又把主意想了一回,觉得万无一缺,袁训的心思又回到金殿上。他的万无一缺主意,就是由今天金殿上听到的消息而更加圆满起来。
宫门已经下钥,但御书房中灯火通明。都是才从御宴上回来,陈留郡王,项城郡王、辅国公、兵部尚书等人看上去都精神饱满,没有商议一个下午后的疲倦。
皇帝居中坐着,抚须看向吏部尚书梁大人:“梁卿,你还有什么说的?”吏部尚书心想我岂止有什么说的,我压根儿就不能答应。
总算轮到他开口,梁大人一出声就火星子直迸。也不能怪他恼,是两位郡王说话没道理,按他们说的……梁大人恼道:“按郡王们说的,今年武科中的人全跟着你们走不说,还要声明不论官员平民,只要武科上有名次的全从军?皇上!”
梁大人气得胡子抖动:“平民们这样办也就罢了,怎么还加上官员们的名字呢?”
陈留郡王冷淡。
项城郡王冷笑。
他们两个人虽然不和,但这件提议上完全吻合。
郡王们在边城出生入死,却听说京里调不出人。西山大营不过只走一部分,就哭爹喊娘,到处钻营,倾家荡产的贿赂,只求不去边城。
梁山王听到这消息都拍案骂了娘,何况是在外的所有郡王。郡王们不依,在例行会议的那天,一起炮轰京里这些软包蛋,陈留郡王和项城郡王就是那天吵起来的。为了争人是起因,恼怒软包蛋们是诱因。
两个本就有嫌隙的人,先是会议上吵,吵得不过瘾,回去拉人马就打上一架。梁山王喝斥不下,他也生气,他并不用心去喝斥。借着这个机会,全军回来修整,再把陈留和项城打发回京,你们京里面吵去。
到京里面好好嘈嘈你们缺人,让软包蛋们都听清楚我们是怎么流血掉脑袋的!梁山王也有看笑话的心,天子脚下的兵不先出来,我们在外面就打不动了。
陈留郡王和项城郡王都不是吃素的人,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提出武科的人去边城,他们还嫌不行。再加上一句,凡官员愿意卫国者,都可以去武科。
梁大人管吏部,他要是不恼他就傻了。
官员们归我管!
不归你们郡王调动。
梁大人口沫纷飞,脸涨得通红,据理力争:“一则不合体制,二来当兵的军功丰厚,官员们全贪银子去当兵怎么办?”
文也行,武也来得的文官还真是不少。而私下抱怨没差使的官员,也是一样的不多。
面对梁大的反驳,项城郡王冷笑连连:“能有出来的人,那倒不错!至少我夸赞一声!”陈留郡王在这种时候要和他一心,征兵的事情两个人再不一心,这趟京城就算白回来。陈留郡王也跟上:“会有出来的吗?”
“你们……发自己私意!”梁大人心想西山大营不肯去,你找兵部去,当兵的不归我管。他看似表面怒火冲天,其实这是在君前,梁大人当心着呢。他觉得脾气也发得足够,就势儿一转,把话题抛给兵部尚书。
“牛大人,您看这是你们兵部的事情吧?”
不想牛大人比他还要滑头,他抽不出人来给郡王们,以后打仗不利的责任,他担不起。郡王们要怎么征兵,只要皇上答应,牛大人没意见。而且心想多扯一个人下水,以后多一个人担着。
就一本正经,反而把梁大人斥责:“梁尚书说话理不当!军功丰厚是朝廷按例,并不是我私放的!再来军功丰厚,官员与平民都能得之才是。依梁大人的话来说,只有平民们能当英雄,当官员的空有抱负,也只能干看着?”
梁大人恼得一头子急火,心想你们兵部还要插手管到文官上面来吗?但不能再吵,就只瞪住牛大人,在心里狠狠的骂,我把你这头坏透了的老牛,我今天晚上回家去大嚼牛肉。
没有人再说话,就都看向皇上。
皇上的心里却是愿意的。
他自知太平世界里登基,又一生都在太平世界中。这么的太平,自然与边城苦战难以分开。年前调西山大营的人前往,扯出一件又一件的官场污糟事,皇上自知从梁山王开始都有不满。
梁山王常年不回京中,不用说是劳苦功高。民间是独子不征兵,可梁山王只有一个儿子,去年就上奏折,奏请独子入军中。
别人几个儿子里抽一个都不肯去,装有病的,临时摔断胳臂腿的,反正以后接巴接巴还能长好……皇上可以体谅到梁山王等人的寒心。
他本着安抚他们,也得答应陈留郡王和项城郡王的提议。下午金殿下已经讨论一下午,皇上见到文官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因为这提议是官员们可以去赶武科,并没有强制官员们去赶。你不去,也就不会征到你。
因为只有吏部尚书等几个人激烈反对,认为触犯到他们的权力。别的人都没意见,我不去不就得了。
再来陈留郡王和项城郡王是为了争兵将才打到京里来,只要有兵将,他们的矛盾自然解开。
皇上就目视坐在这里的臣子,痛心疾首地道:“朕自登基以来,国泰民安,雨水和顺。这上仗上天鸿福,下仗黎民百姓。再有无数将士们流血丧命,无数官员们兢兢业业,才有这太平的大好河山,”
梁大人听到这里就傻了眼,完了,皇上这意思是他要松口答应。
完了,这个先例一开,以后吏部就归兵部管了。郡王们说一声缺人,满朝官员就都归他们调动了。
尚书大人怒火满腔听着皇上一一道来,最后拍板郡王们的提议很好,就依着他们说的办。从明天开始,京里京外张贴告示,声明官员们和平民们同例。明天上朝,就发布这个旨意。明天下朝,就往各省去信,京里的官员都这样办理,外省的官员也是一样的办理。
尚书梁大人失魂落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御书房。失一着,则失千着。以后这将成为旧例,吏部的威风从此丢在自己手里。
身边是三三两两同出的官员还在私语。
“有人会去吗?”这些能进出皇上御书房的官员,他们都有丰厚的官俸,他们是不会去的,也就一时想不出来谁会为这个去当兵。
完全震惊去了!
旁边走着陈留郡王和项城郡王,官员们悄悄儿的打量他们。这两位哪里是来打御前官司的,他们分明就是来诉委屈的。
这委屈诉的,皇上也不得不让步,以他们说的为齐。
牛大人则喜上眉梢,在梁大人恼怒时,牛大人也同时看出这是扩大兵部权力的机会。他乐呵呵地过来兜搭:“武科最后一场那天,圣命两位郡王前往主考,你们可以自己挑选,自己相看……”
才说到这里,一旁跳起老高一个人。梁大人喝命家人:“晚上给我备牛头汤,煮牛心,烹牛肝,挖出牛胆来泡酒!”
与他同行的官员没明白,诧异地劝阻:“梁大人,您不是用过晚宴,还是宫里用的,莫非没吃饱?”
梁大人咬牙切齿:“我宵夜!”继续叫家人:“那老牛皮给我留着,我吃多了抽打他一百鞭子,消消食。”
陈留郡王忍住笑,眼角见到项城郡王也似笑非笑,也把个眼角瞄过来。两个人眼角碰上,都冷上一冷,随即避开。
这两个人,还是不好。
静夜的外宫中,梁大人要抽打老牛皮传得很远,牛大人就离他不远,不可能听不到。牛大人慢条斯理,也吩咐自己家人:“小行子,我们家那闲房子的梁头,总是碍人眼睛。回去扯大锯,锯开个百十来段,方趁我心。”
家人却还糊涂着,正羡慕梁大人晚上不睡吃那么多,家里有钱。又笑话梁大人抽打老牛皮又有什么用?还不如买贴消食的药熬煮喝了管用。
听主人吩咐锯梁头,家人吃惊:“这这,锯了梁那房子还不塌了。”牛大人笑得阴森森:“锯那无用的房子,无用的,谁还怕它塌呢?”
再糊涂的人也就听出来这一对人的火药味道,这两位全是尚书大人,别的人不敢惹事情,帮谁都不好,见宫门在即,各自回家。
梁大人叫着煮老牛汤,牛大人叫着锯梁头,也各自回去。
陈留郡王上马后,回首这些人背影冷笑。
怕死?
就我们是不怕死的吗?
今天这事情很趁他心意,他候着辅国公上马,对他展露笑容:“岳父,说驿站里有文章侯府送来的席面,我们回去喝几杯。”辅国公欣然,他想的还有别的:“今天外甥媳妇又送来有好吃的,你我中午晚上都是宫里吃的,驿站里的就余下来,正好回来吃,也许还有妹妹给我亲手做的呢。”
陈留郡王大笑出来,带马凑到辅国公耳边,低笑道:“我和您打赌,您是接不走岳母的!”这件事正是辅国公心中的忧愁,见女婿过来扫他兴致,辅国公假意吹胡子瞪眼睛:“胡说,我自有分数。”
这一对翁婿也打马去了。
袁训知道官员们可以上武科,就是他身为官员,下午在金殿上听到的。
辅国公翁婿出宫时,袁训正让宝珠扯着看东西。袁训看书的侧间里摆了一地,几上桌上也全摆满。
宝珠嚷道:“这是我铺子里凡有的东西,我全让各取一份儿来,你说哪些是舅父姐姐会喜欢的,哪些是他们当地没有的,”宝珠遗憾:“下午我听姐姐说话,说她长这么大,和舅父是头一回进京,就是舅父,也是二十多年头里才进过一次京,我说以后常来往的好,不然母亲岂不伤心呢?”
别说母亲伤心,就是宝珠也会想念的。
当姐姐的对弟妹有微词,但当弟妹的却是一片真心的对她。陈留郡王妃要是知道,也应该含愧的吧?
袁训随意应着:“哦,喜欢。”心里却在想御前会议应该结束了吧?想来皇上理当答应姐丈和项城郡王的提议才是。
宝珠见他心不在蔫,拿个肥白拳头又过来,在表凶眼皮子下面晃动着笑:“回魂来的哟,还没当几天的官,就家事国事分不开了吗?”
“不是,是想宝珠。”袁训回神,想想自己不久就要离开,趁在家里的这几天光景,更要疼爱宝珠,和她好好的玩耍才是。就再取笑上来:“想宝珠才会走神儿,”又装出来后怕模样:“幸好你家夫君我不是一般人才儿,在衙门里见上司倒不想你。”
宝珠就甜蜜的笑,打趣他:“你想,你怎么不想呢?乱想我,挨板子我才笑你呢。”又把旧日的笑话取出来夫妻调笑,宝珠眨动眼睛,好似天上的星辰:“可想过那王府的姑娘没有?”
“想,怎么不想,不想宝珠的时候也想她。”袁训嘻嘻,又坏上来。
宝珠佯装恼怒:“放老实!”抿着唇儿自己笑,你连王府的姑娘都认不得,还敢来骗宝珠吗?
宝珠可不上当。
第一百七十五章,宝珠不上表凶的当?
第一百七十五章,宝珠不上表凶的当?
同类推荐:
偷奸御妹(高h)、
为所欲为(H)、
万人嫌摆烂后成了钓系美人、
肉文女主养成日志[快穿系统NPH]、
娇宠无边(高h父女)、
色情神豪系统让我养男人、
彩虹的尽头(西幻 1V1)、
温柔大美人的佛系快穿、